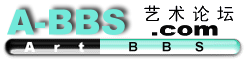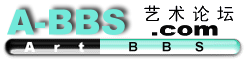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1-11-25 00:28:17
□ 阅读次数:2127
□ 现有评论:6
□ 查看/发表评论 |
|
|
中国绘画通史(上下)
王伯敏
|

前言:
《中国绘画通史》己卯序
不论是美术史还是绘画史,都是当今人文学科的一门显学。它所评论的,固然是美术家、画家的聪明才智,然而,它所赞美的,却依然是人的存在,人的既有和应有的价值。这门学科,需要较多的学人关心、支持,促使它充实、拓宽并深入。
本世纪中国画学史的进展,分两个大阶段:一、本世纪的上半叶为上阶段。美术史家继承古代治史传统,重视文献资料,以画家作为画史的主人公,以卷轴画作为绘画发展的实例,着重笔墨分析,寻求流派的渊源;二、本世纪下半叶,亦即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下阶段。多数美术史家重视文献之外,把视线转移向田野考古领域,新发现的岩画、帛画,现存寺院、石窟壁画及民间绘画等等,都因此而被充实到史册中。在这个阶段,史学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还在于观念与治史方法的改变。美术史家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梳理、综合各种历史现象,侧重于美术在各历史时期的生发与演变规律的探索。在这阶段,高等美术学校设立科系,专门培养了美术史研究人才;与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频繁交流;国内举办的有关美术史研究的讨论会不时召开;更由于美术史家在思想方法上的提高,在研究上做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努力,遂使绘画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上了新台阶。
本世纪的下半叶,我作为美术史学队伍中的一员,在这个行列中度过了50个春秋。从事研究的过程,无非“读书”、“行路”和“思考”。由于本职工作责任感的驱使,也由于专业研究兴趣的推动,再就是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我先后完成了六种美术专史的编写。我这部曾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今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的《中国绘画通史》,就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绘画通史》,着重于对绘画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阐释民族形式的形成在东方以至世界的影响。我尊重传统,珍视前人的成果,而又要求自己尽一切努力对本问学科做出开拓。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走在学术朝圣的大路上,要想突破某种局限而迈开大步,非有勇气与毅力不可。早在十多年前,曾有记者来访,询问我在治史的过程中做了哪些较有意义的事。我在回答时提到,我在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严格要求自己画出一条足以体现中国画学发展过程的直线,尽可能做到将各种绘画的审美懿采,归纳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对此,我曾不懈努力。可是,这条直线不容易画,因为历史上有不少虚假现象,似一片云雾,稍有疏忽,便会阻碍某条支流的畅通。历史悠久的中国绘画,有民问画、宫廷画、文人画三大块。就思想领域而论,儒、释、道之外,还有诸子百家,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作用,往往不容治史者稍稍的忽视。这条直线,又如一股由许多细线相绞扭缠而成的绳索。何况,这条直线(经)还要与纬线做必要的相交穿插。诚如翦伯赞在《历史“金燧”的规律》一文中所说,“吾人又将如何迅速捕捉这一霎那出现的‘奇观”’。对美术史主人公的前言往行,既要“究其辞”,又要“通其义”,在描画时,还得“删繁去冗,举要提纲”,才能使这条直线刚健充实而辉光日新。虽然我还达不到,但为此,我一度潜沉下来,扎实地做了一些个案分析工作,企图以简括的方“式,通过局部来窥测整体的连贯性。不意在做个案分析时,却得到了另一个启发,即画史的编著,必须有利于今后绘画的创造,从而涉及到如何将现时代的绘画与永不重演的历史绘画相联系的重要问题。我的治史过程,虽不能谓之成功的经验,总可以言之为“有益的教训”。三年前,我曾作小诗云:“年来治史走四东,白发时添耳半聋。”确然是,我的发白耳聋,至少与努力画这条直线有关。
自建国以来,50个春秋行将过去,美术史家的足印,一个又一个留在了不平坦的前进道路上。“文革”风暴刮起,美术史研究被迫停顿了。一停顿就是十个年头,这个损失是惨重的。改革开放后,文艺得以复兴,人们精神振作,忙着把夺去了的一部分时问补了回来。学无止境,我重操旧业,“春秋万里行,寒暑一床书”,又将数万张沉睡着的学术卡片启用了。根据我的工作习惯,教学之外,便是“煮茶、琢璞”;倦了,则以“看山、画山”来作为生活调节。我之所以把“治史”比之为“琢璞”,意在表示绘画史这门学科有它的重要性,也表示治史的艰巨性,更表示治史要有一种责任心。尤其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需要开发、维护并深入研究的今天,作为人文学者的美术史家,应负什么责任,就不能不提到议事的日程上。际此世纪之末,展望美术史学的未来,晨光灿烂,我们无不欣欣然而高歌。我们回顾百年来的历程,可以预料,进人新的世纪,在美术史、绘画史及其他美术专门史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多更新的著作出现。这一新局面的诞生,虽然会经历一个艰辛的孕育时期,但是,可以相信,我们的美术史家有智慧,能把责任心加强,困难必会迎刃而解,那个时候,美术史和绘画史的新的出版物将如潮涌般出现。届时,人们登高揽胜,与时代同步,则新一代的美术史家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必超前人。在这门学科的史学史中,他们必将谱写出更辉煌的一页。
--------------------------------------------------------------------------------
内容简介:
本书纵横古今,论述了自原始时代以降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对画事、画家及画作均有系统地加以评介,涵盖及卷轴画、岩画、壁画等备领域。书中更增补了最新出土资料一百三十余处,资料翔实,插图丰富,是迄今最完备、最全面、最具规模的一部关于中国绘画发展史的学术专著。
--------------------------------------------------------------------------------
作者简介:
王伯敏
生于1924年。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史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1992年国务院表彰王伯敏“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予以国家奖励的殊荣。王伯敏著述宏富,编著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绘画通史》等五部美术史著作。其他尚有《中国民间美术》、《中国画构图》、《山水画纵横谈》、《唐画诗中看》及《古肖形印臆释》等三十多种著作问世,在某些方面填补了我国以及东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并有著作被译介至国外,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的优秀“带头人”。
--------------------------------------------------------------------------------
作者自述:
本书,是在我编写的《中国绘画史》基础上重新撰写的。一是增加了内容;二是适当地调整了时代的划分;三是把时代延续到了民国。而且,定书名为《中国绘画通史》。
我原来编写的那部《中国绘画史》,198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那部书的完工时间是1965年冬天,不意碰上了“十年动乱”的日子,稿子被堆放在一处阴暗的角落里,几乎成为蠢虫的食料。“动乱”结束,那部稿子才得以付梓问世。出版时间竞拖延了17年。
1994年3月,我应邀赴台湾,出席由台湾省美术馆举办的“现代中国水墨画学术研讨会”。会后,见到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董事长刘振强先生和受该公司特聘的美术丛书主编罗青先生,谈到了我在那里出版的《唐画诗中看》,也谈到了那部《中国绘画史》。当我透露有重写中国画史的意图后,刘、罗两先生热情地表示愿意并欢迎出版这部书。不久我回大陆,经过进一步的联系,这部稿子的出版就这样定下来了。
编写美术(绘画)史,我向有两种不同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一是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二是有兴趣,有乐处。我之所以感到艰巨,不仅仅由于我国历史悠久,画史内容繁复,头绪万千,便是对待新出土的文物,也觉得应接不暇。大陆的文物天天有出土,田野考古日日有新的报道。1994年5月,我避暑胶东,去了没几天,便获悉当地海阳县盘石镇嘴子前村又发掘出春秋墓葬,不但有大量铜器,而且还有漆绘的木器。接着,又听说淄博的博山区发现了金代的壁画墓。我前往做了实地的调查。刚回来,又听说安丘发现了宋代的石棺墓,而且有壁画。接着,一位朋友来函,惠告洛阳浅井头近年发现西汉墓壁画的具体情况,又有友人来信报道新疆库木吐喇79窟壁画三次重绘的历史情况……类似这样的新发掘、新发现,直接涉及到绘画史这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我们能等闲视之吗?我出版过的那部《中国绘画史》,从完工到现在,足足过去了三十多个寒暑,在这期间,我经过两部大型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和帅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的主编工作,深知还有不少新发现而且有很大价值的新材料,在我那部绘画史中是没有的。现在,当我计划重写本书时,心里安能不着急,又怎么不因选择并增补新材料而感到工作的艰巨。
出土的新材料,除一般报刊与内部通讯报道外,就《文物》、《文物天地》、《考古》等刊物的所载,也足以使人瞠目。便是新开发的深圳市,在短短的IO年中,境内已发现古文化遗址(点)109处。全国范围内,不论是在西北或中原,那些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青铜时代的铜器,还有如汉代的帛画、画像石、墓室壁画等等,这些遗迹的新发现,有的足以使你改写其历史,有的可以使你纠正过去的偏见。我们曾认为,像卷轴画之类的新材料不会在出土文物中得见。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在山东邹县明鲁王朱檀墓出现钱选怕莲图》,被认为千古奇迹后,人们还以为这只能是极个别的事例。但是,谁能想到,在我的那部《中国绘画史》出版的那一年(1982年),江苏淮安县(今改市)东郊闸口村,发现明代富商王镇夫妇的合葬墓,就在这座墓葬中,竟出土了有明代夏昶、谢环、陈宪章等所作的25幅书画。令人不可思议的,这批被分别置于墓主人两腋之下的书画,自明代弘治九年(149年)入士以来,与墓主一起“长眠”在地下近五个世纪之久,居然基本完好。
这里,我不能不再提另一方面工作的艰巨性,比如计划重写本书时,想把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史补充进去,希望使一部中华民族的绘画史编写得更全面。但是,我只是这么想,却未能实现。首先,这要考虑到本书如何搭构新的框架,又如何建立新的编写体制。问题还接踵而来,不少突出的矛盾,使得你一时无法解决。事实上,这不是一部书的量的增加,它必须突破原来的编写框框,才能使一部多民族的庞大的专题史作出有系统的新的表达。因为“系统”不是简单化的一种排列,它必须“削枝理节”、“纵横穿插”,才能使全书有机地、又是很有默契地容纳下具有上下数千年历史、覆盖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主要史迹。在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不仅有各自的内涵与特点,在历史的发展中还有相互渗透、交错以至同化的情况。如果只给以各个“分割性”的评介,必然会失却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全貌。反之,只顾到多民族文化的整体全貌,又会失却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个性与它的特殊性。绘画艺术史,不是某一种技术进步的历史,它是一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民族性格变化的历史。说实话,前几年,我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尽管尽了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只采取简便的方法,将55个民族,分为55章。虽然,脉络被整理出来了,却还未能更好地做到,在编写的体制上,体现出各民族美术在各历史时期,通过相互渗透、合作与同化的关系而丰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平常,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灿烂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在美术史的编写上,如何体现这个“共同创造”的复杂性与优越性,倘若没有一个合理的框架与科学的结构是难以办到的。看来对于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美术史学界,还有待深入探讨并做出必要的努力。
至于说到“有乐处”,还需要加一句:“苦也在其中。”苦与乐是对立,但又往往何其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时为了查对一个地名或一个年份,可以累得你满头出汗,那种苦,惟有自己才知道。及至找到了资料,那时的高兴,也惟有自己才知道。有时思考一个疑题,好像碰到了“鬼打墙”,任你怎么也转不出来,于是沉闷不堪,支颐案头,苦恼之至。不意睡了一会,或换个地方读了几首诗,忽然开窍,有似神助,转出了“鬼打墙”,因此额手自庆,开心之至。苦与乐,竟是如此交替着。
再说,我的所谓“乐”,不仅仅在于顺利地找到了研究资料。更有意义的,还在于中国绘画在漫长发展的历程中,许许多多的事件,令人不得不为之兴奋,不能不为之自豪。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无数有慧悟的画家,他们提出了许多既有深度,又带有哲理性的绘画名言,如“迁想妙得”、“遗貌取神”、“万趣融其情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及“内营丘壑”等等。他们在绘画创造上又是巧夺天工,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感受。无论画千军万马,写五岳三山,或画一花一草,无不引起千百万读者的共鸣。他们“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认真到了极点;落笔取舍时,他们是“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要求又何等严格。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从巨幅到小品,都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法国史论家丹纳说:“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艺术哲学》第一章‘它术品的本质”)一卷优秀的风俗画,可以让几世纪后的观众俨如置身于那个时代的市井中;一卷精妙的《溪山无尽图》,或一轴《千岩竞秀图》,会把读者引导到大自然的纵横万象中,从而领略自然造化的奥秘。我们古代聪明的山水画家,还大胆地突破时空对于画面表现的局限……我们研究并编写古代的绘画史,接触到这样一系列的古代名画时,能不乐在其中?1982年,我有诗《跋“中国绘画史”稿》,最后几句记述了成稿后的愉快情景。小诗云:“……春申付梓日,高歌在钱塘。细研松烟墨,纸上尽苍苍。举头山水绿,回首闻茶香。”我高兴地作画吟诗,举头既喜“山水绿”,回首又闻茶清香,这对文化人来说,如此之乐,难道还不够尽兴吗?
世界上的诸多学术研究领域内,美术(绘画)史无疑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也是文化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在本世纪的80年代,曾有人强烈表示相反意见。有这样一位人士,他收集了东西方出版的好多部美术史著作,其中也包括了我主编的那部《中国美术通史》,他居然出奇地把这些美术史书统统泡在水缸里,使它发涨变形,然后取出晾干。他就把这些变了形的“半纸浆型”的出版物在西欧一个大城市展出,还告诉人们:“过去了的美术,不必提它,编写美术史是多余的事,这种著作,有碍现代美术家的创作情绪,也有碍现代美术的发展。”(大意)当然,绝大多数的美术家听到他的话都会嗤之以鼻。试问,历史能割断吗?只要不是无知,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人民能不需要研究并熟识自己本国以至世界的文化历史吗?这是因为,研究历史,归根到底还是尊重人的存在与价值。
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的著作,自陈师曾于1922年公开出版以来,迄今出版已有十余部,断代史有三部。说实话,对这方面的研究与出版是不够丰富的。本书,已完成于本世纪之末,希望不久的将来,能见到又一部崭新的中国绘画史的问世。此外,我还有一个希望,希望能出版一部《中国边疆绘画史》。中国的陆上与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为邻,海上与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相望,因此,编写与邻国相关的边疆绘画(美术)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古贤云:“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实则“已学者”可以再学,况“未学者”,更要换而不舍。愿与美术史论界同仁们共勉:“朝骋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我们将“巳复旦兮”,“更上一层楼”,迎接对新世纪到来的曙光。
1995年夏于杭州南山
重构中国绘画的历史 / 巫鸿任
北京三联书店将出版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通史》,我知道了非常高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我看来这部书是现代中外美术史家所著各种中国绘画史中取材最为广泛,构思也最有创造性的一部,由三联书店出版推广可方便广大中国美术爱好者对我国绘画史的学习;二是因为著者又才本书范围和取材的考虑并非仅仅扩充了中国绘画史的知识范围,而是同时也更新了收集和使用历史素材的手段方法,因此对中国美术史的一般性研究也有方法上的意义。举例说明这后一点,王先生在谈到他希望把本书写成一部多民族绘画史时说的一段话十分有代表性,可以作为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史学观念的一把钥匙。在他看来,任何对绘画史内容的扩张并非仅仅是量的增加,而必须突破原来的写作框架:
因为“系统”不是简单化的一种排列,它必须“削枝理节”、“纵横穿插”,才能使全书有机地、又是很有默契地容纳下具有上下数千年、覆盖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要史迹……绘画艺术史不是某一种技术进步的历史,它却是一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民族性格变化的历史。(见著者序)
可以说,作者在取材和结构等方面所做的革新都是为了这个中心的,即把一本绘画史写成一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民族性格变化的历史”。读者在阅读和使用这部书的时候会对本书的特点各有领会,我在这里只略谈一下我所感受最强的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史料的扩充,特别是作者对考古材料的大量应用。我想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单纯扩大知识范围的问题,因为对某一特定类型材料的注重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所写历史的范围、内容和性格。以往《中国绘画史》多以传世绘画和画史记载为主要素材,即便近年来学者不断尝试结合使用考古材料,但这种使用一般说来仍是局部的和辅助性的。王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在他的笔下考古材料往往对重构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具有了决定性意义。这一特点在其对宋以前绘画的讨论中尤其突出,但即使是宋、辽、金阶段,他所大量引用的墓室壁画材料仍使读者对这一时代的绘画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考古材料的大量运用导致“绘画”概念的扩大以及绘画史叙事模式的改变。虽然不少以往的美术史家也在其对中国绘画的讨论中包括了石窟和墓室壁画、画像石,甚至器物装饰,但是重心无可置疑地仍在卷轴画上。这种偏重在研究宋代以后绘画的时候可能问题较小,但在研究宋代以前绘画时则大有问题,因为唐代和唐代以前这门艺术的大宗应是建筑壁画和其他类型的装饰绘画。本书唐代一章可以说是比较切实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情况,把大约一半篇幅用于分析石窟和墓葬壁画,同时在对画史所载画家的讨论中特别突出吴道子这位出身工匠的壁画大师。
对考古材料的重视也把中国绘画史从单纯的书画鉴定中解放出来。举例来说,绘画史著者常常在某些传世卷轴画的真伪和断代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确凿无疑和时代有据的绘画作品却往往被放在了一边。本书则一改这种偏见,如讨论隋代绘画的时候,著者对一些重要画家和传世作品(多为后世摹本)作了简要介绍,而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敦煌石窟中所保存的隋代壁画,尤其是303窟中的一幅13.5米长的风景画。以著者的话来说,“与现存古代的长卷山水比较,它是一件较长又较早的作品”,对研究山水长卷的发展至为重要。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关于本书的结构。实际上,考古材料的积累已经使得一部中国绘画史不再只是一部以宋以后一千年为主的“卷轴画史”。这部历史的前半大大地充实了,原来资料十分贫瘠的上古、商周时期现在有了不少实际绘画形象,除较熟知的彩陶和画像铜器以外又增加了岩画、地画和帛画。但著者所做的另外两项创新同样对改变绘画史的结构和叙事模式起了重要作用。一项是他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如本书唐、宋、明清各章都包括对民间绘画的专论,列举有关当时艺人和作品的资料,绝非泛泛而论的简介。另一项是他对近现代美术的重视,使这部中国绘画史不仅是一部古代绘画史。全书最后一章专论20世纪前半绘画,讨论重点除重要画家外包括绘画社团和美术学校的出现以及漫画和月份牌等大众艺术的流行,洋洋洒洒百余页,可说是自成一部简明民国时期绘画史。
当然,没有一部美术史是完全客观的。特别是在观点、传统纷纭的今天,美术史写法的差异往往反映了作者的选择。但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应该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新史料做最大程度的利用,同时对艺术史的史学规范不断进行反思。王伯敏先生的这部《中国绘画通史》在这两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巫鸿
2000年5月于北京
(巫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执该校“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 王伯敏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出版日期: 2000年12月
版次: 第一版
国标编号: 7-108-01373-8/J
作者国家: 中国
页数: 694
定价:¥136.00元
|
|
现有评论:6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