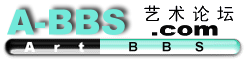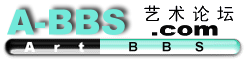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4-06-20 11:49:02
□ 阅读次数:3759
□ 现有评论:1
□ 查看/发表评论 |
|
|
不守法的使者(图文本)
止庵
|

--------------------------------------------------------------------------------
现代派画家是一群 “不守法的使者”--他们笔下的世界,不拘美丑,纵横虚实;他们作品中有着天才般的领悟和震撼;他们是莫奈、高更、梵高、杜尚、达利……画评家止庵,打破 “画”与“文”之间的藩篱,以300余幅现代绘画作品和80篇随笔,穿梭于艺术、人生、历史、文学之间,完成一次与现代派绘画大师之间真正的心灵对话!
--------------------------------------------------------------------------------
前言:
我见过莫奈晚年的一张照片,画家站在他的大幅画作《睡莲》(1914-1926年)前面,手里举着调色板,似乎满眼都是迷惘。老画家这时已经功成名就,但是约翰雷华德《印象画派史》说:
“正像安格尔一样,他死的时候,是他所体现的思想早已过时的时候。莫奈是印象派画家中第一个成功的人,是亲眼看到印象派真正胜利的惟一的印象派画家,他活着亲身感受他的孤立,当他看到许多年才实现的幻想被年轻一代十分激烈地加以攻击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一些痛苦的。”
其实印象派中也并非莫奈一人落入此种境遇,迈克尔·列维《西方艺术史》说:
“德加、莫奈以及雷诺阿却都是特别地长工寿——一直活到马蒂斯和毕加索创作旺盛时期。至少从历史上讲,他们都从杜尚那‘暗号性的’作品《泉》中看到了一种清醒重大的想法。”
我们曾经慨叹于另外一些印象派画家如莫里索、西斯莱,特别是弗雷德里克·巴齐耶(Frederic Bazille)死得太早,来不及享受自己事业的最终成功;当然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更为大家熟识的凡·高和高更,他们身后的巨大荣誉与他们本人的不幸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对莫奈以及稍早于他辞世的德加和雷诺阿来说,“特别地长寿”似乎成为一种缺憾。这个事实近科残酷:现代绘画确实变化快得让人难以接受,甚至画家们都来不及退场就看见自己当初的创新已经变成落后了。这是一部创始者与终结者聚集一堂的有点儿怪诞的历史。我们可以在莫奈和雷诺阿最后阶段的绘画里发现他们对风格的特别强调和发挥,似乎也是有意与所处时代相抗衡,这无疑构成他们一生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对那一时期的艺术史来说则未必有多大意义,他们毕竟已经过时了。
在我们涉及到的这一段历史里,此后还有不少类似这样的画家。一方面,不管以名计抑或以利计他们都是成功者;另一方面,还有漫长的余生不知该怎么度过。与前辈们比起来,他们不过是成功得相对顺利一些罢了。似乎现代艺术史上大部分的困厄都让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代为领受了。较之后来的那些破坏者如毕加索、杜尚等,无论如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些“好人”,甚至想要带着自己的特色加入传统,就连其中最“坏”的塞尚也还一直渴望能被官方沙龙所接受呢。传统对待他们实在过于严酷了。而传统也在与他们的长期对峙中耗光了元气,以后遇见真的充满恶意的对手反而不堪一击。印象派画家所关心的“光”与“色”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一点改变,但是改变一点也就意味将要连带着改变一切。看着莫奈那张不能让人感到愉快的照片,我疑心他或许在想:凭什么你们就这么容易呢。我的朋友Morin谈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苦苦挨过的十九世纪后半叶时说:“我恨死了那个时代。”这正好与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对那一时期的追慕和怀想成为对比,但是我们实在难以接受当初凡·高绝望自尽、高更抑郁而终这类事实。《现代绘画辞典》关于高更说过一段话,似乎也与茨威格的意见相左:
“事实上,他的一生难道不就是一种长期的折磨吗?他的妻子、同事、朋友、画商、殖民官员和整个社会似乎在合谋,以造成他的失败,以杀害这个具有画家缺点的人。他并非甘心地被不怀好意的同代人视为一个饿肚子的流浪汉,一个无耻的逃兵,而他败坏的历史恰恰又是他艺术的成功之路。”
但是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现代艺术上毕竟还是让包括高更在内的一批最有才华的国家得以充分展现才华的时期。代价是一回事,成果是另一回事。的确相对于很多画家活得太长,另外一些画家活得太短,不过我感到这个长短似乎仅仅涉及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功与否,而对他们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构成寻常想象的那种障碍。凡·高和莫迪里阿尼就人生而言都是不幸的,就艺术而言却很难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尚且有待于完善的。修拉只活到三十一岁,在这个年龄马蒂斯几乎全无业绩,然而马蒂斯以后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儿地成就自己,修拉则已经把一生所要做的都做完了,实在无法想象他还能画出比《大碗岛》更加完美的作品。最终修拉和马蒂斯作为艺术家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现代艺术史像一块从悬崖滚落的巨石,速度越来越快;而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是把巨石推上悬崖的人。大概正因为历史不在某处过久停留,绝大多数画家都足以完成他们具体的贡献。问题倒是在另一方面,即前述莫奈等人所面临的那种困境。这个似乎只有毕加索多少能够避免。虽然评论家对他的后期成就亦有微辞,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有太大的创造力使得他不断变化风格,形成自己若干不同时期,从而始终努力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并不特别喜欢毕加索,但是非常钦佩他,在现代艺术史上,若论创造力他到底还是占据第一位的。当然更具启发性的是杜尚,罗伯特·马塞韦尔在《杜尚访谈录》的序中说得好:
“当毕加索被问到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不是艺术?’毕加索作为一个画家,要的是界线。而杜尚作为一个‘反艺术家’恰恰不要界线。从他们各自的立场来看,彼此都不妨认为对方是儿戏。采取他们两人的任何一个立场,就成了一九一四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艺术史的重要内容。”
他谈到“立场”,毕加索的立场与印象派乃至更早的画家们并无二致,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困境,而他只不过是在此立场上试图解决他们所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已;杜尚才是提供一个新的立场因而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人。然而杜尚是惟一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可能被仿效,所以并不一了百了地替同时以及此后的画家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杜尚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启发性。
皮埃尔·卡巴内在采访杜尚时提到“不守法的使者”,我想对一个真正的现代艺术家来说,这是最有概括性的话了。在那本谈话录中,杜尚说:
“一九一二年有一件意外的事,给了我一个所谓的‘契机’。当我把《下楼的裸女》送到独立沙龙去的时候,他们在开幕前退给了我。这样一个当时最为先进的团体,某些人会有一种近似害怕的疑虑!像格雷兹,从任何方面看都是极有才智的人,却发现这张裸体画不在他们所划定的范围内。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线了,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我冷静了。”
他道出了自己毕生追求的真谛,也让我们明白他对整个现代艺术的最大贡献究竟是在哪里。对杜尚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既定模式,真正有生命的艺术永远是不合规范的,否则它就死了。杜尚画《大玻璃》至少有一个意义就是像他指出的:“它是对所有美学的‘否定’。”同样从这一立场——实际上他是超越了所有立场——出发,他为被评论家和超现实主义者斥责为“作品和画家本人良知突然黯谈无光”了的德·契里柯辩护。杜尚说:
“他的崇拜者无法追随他,于是便断言德·契里柯的第二种样式丧失了第一种样式的生命力。不过,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发言的。”……
--------------------------------------------------------------------------------
内容简介:
就 “现代性”而言,一百多年来在绘画中比在文学中表现得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现代人理应与现代绘画发生广泛共鸣。本书由八十则随笔和精心选择的三百余幅现代绘画作品构成,随笔是绘画的解读,绘画是随笔的延伸。作者将读书与观画有机统一,提供了一部新颖独特的现代绘画文本/画册,读者自可阅读/观赏,体会 “现代性”。
--------------------------------------------------------------------------------
请读片断:
萨尔瓦多·达利
“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达利的话提示我们,他始终是“没疯”地表现“疯”;而无论是在画里还是在画外,能够把这种表现贯彻得如此彻底,又印证了他与此类似的另一句话:“超现实主义者与我的差别,在于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达利”几乎与“超现实主义”成为同义词也不无道理。荣格关于毕加索所下的考语,用在达利身上或许更合适些:“这个人不肯转入白昼的世界而注定要被吸入黑暗,不肯遵循既成的善与美的理想而着魔地迷恋着丑与恶。”
在我看来,作为行为艺术家的达利在公众面前成就了画家达利,但是在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心中损毁了画家达利。关于达利,除了他太多的近乎胡闹的举动和言论之外,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无比精确的写实主义、“偏执狂批评方法”和一系列因此而产生的著名形象,如柔软的钟表、腐烂的驴子和聚集的蚂蚁等。达利喜欢最真实地表现最不真实的物体和情景——这旬话中的两个“最”字没有任何保留意义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所以他的作品如《启发性的愉悦》(1929年)、《愿望的调节》(1929年)、《内战的预兆》(1936年)、《记忆的延续性》(1931年)、《患有色情受虐狂的乐器》(1933-1954年)和《那喀索斯的变形》(1936-1937年)等,虽然为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烂熟于心,但是严格讲却不可能被模仿。无论技术还是艺术,他都有别人很难具备的充分才华作为依靠。他的“偏执狂批评方法”既是一种努力把自己逼疯的方式,也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启发、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的方式;在对现有形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异方面,达利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可以说达利的画有表演或浮夸的成分;然而他是在做梦而梦怎么能够拒绝表演或浮夸呢。
《新艺术的震撼》指出:达利不把一幅画表现为一个含有全部内在张力的画面而走向相反的极端,把它处理成一个完全透明的窗子;使用他称为一切常用的欺骗眼睛的花招,最丢人的学院主义去引起崇高的思想层次’。”实际上他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点。面对一幅画,我们可能受到眼睛和心灵两重震撼。不妨把达利的梦理解为德·契里柯的梦所启示的无数结局中的一种德·契里柯式的神秘在此转变为达利式的刺激,后者常常具有更强烈的视觉效果若论心灵震撼力却反而不如前者。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画家中以富于想象见长,其中达利可以算得第一;但是达利的想象未免缺乏含蓄或者说,缺乏克制。他的想象的魅力在于其自身,而不在进一步的意味。不过想象本身就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创造,就足以赋予艺术以不容质疑的价值达利画作中的想象是那么奇特,那么无拘无束要说伟大达利也够伟大
--------------------------------------------------------------------------------
目录:
引子
女人
大自然
梦
时代
后记
--------------------------------------------------------------------------------
|
|
现有评论:1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