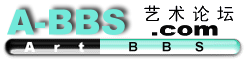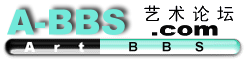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2-04-23 14:04:32
□ 阅读次数:1614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我的西藏之行》
巴荒
|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蔡蓉(笔名巴荒)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独闯西藏阿里无人区的女艺术家。她在1987—1988年中,四次进出西藏高原,三次独行西藏阿里,跨越无人区,辗转于西藏边塞偏远的神秘区域,历经生死疾病,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种种艰难困苦中,进行了历时一年余的考察和艺术教学。
本书以作者数次独往西藏的传奇经历为背景,以其艺术家独特的艺术直觉和理性思考,构成丰富而独特的审美视觉;以贯穿始终的生命体验和对高原的审视,赞颂世界独具魅力的西藏自然和人文景观,赞颂隐匿在荒原中和高原阳光下的生命之质朴、顽强和纯粹;以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张力,在高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的整体与个体生命的交融中游历,传达出民族、艺术和人类不朽的精神。
全书的200余幅图,约9万文字内容,取材于作者4万公里艰辛行程中所拍摄的近万张图片,所作的20万字笔记和艺术创作,以及她来自西藏西部神秘的古格王国遗址的第一手考察资料。本书文字在优美流畅的散文风格和层层递进的结构中,与视觉强烈的图片相随而融贯,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内涵传达出庞大的视知觉信息,是本书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一部方诗办画的艺术杰作,一首苍凉而雄浑的高原与生命的赞歌。
--------------------------------------------------------------------------------
作者自述:
巴 荒
自 述
巴 荒
据我父亲讲,我出生在夜里零点。父亲把我的出生地指给我看:锦江河边,四川大学红瓦村一幢僻静的小楼、他亲手为我接生,但他并不是一个医生。对这一切,母亲总是微笑不语。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的生是属于14日的夜,还是属于15日的凌晨?抑或是15日夜的尽头……一个模棱两可的时间,在一道分界线、一个临界点上诞生的许许多多脆弱的生命之一。不知道那种与生俱来的模糊和神秘感,是不是藉此隐伏在生命之中,使我在追求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价值之时,情不自尽地要探索和表现与此相关的一切——
我的童年与河流、泥土、草木以及鸟虫相伴。50年代初的川大校园绿树成荫。锦江从川大的校门也从我家的后门经过,河的下游两岸都是农田,我家就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交界线上。锦江河在洪水的季节常常是泥浆混浊的,但我喜欢守望这条家乡的河流。遇有机会,我就挣脱大人的手溜到河边一条泥泞的小路,跟着河流走,或等候河的下游走出三四个裸背赤足的汉子——他们神情木然,身体倾斜拖着长长的泥绳;我跟着他们在岸边行走,直到他们和身后的船消失在九眼桥……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他们是纤夫。
我家从锦江河南岸搬到北岸,又从北岸搬回南岸,人工栽培的灌木丛围绕我的家园。受我母亲的影响,我的童年时代处于种植、饲养和采集标本的巨大的热情中、一有空,我就在家门外的菜园子里挖土、浇水种菜或嫁接果木;看着种子埋进土里,再冒出绿芽来,无比新奇快乐。有一年,我把菜园子种成了蓖麻林,把无法在家中喂养的蓖麻蚕统统移到蓖麻叶上放生,那天夜里一场雨,第二天所有的蚕都死了,我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
初中毕业,我成了失学的“病残知青”。象童年一样,我守在家园附近,但昔日的菜园子已被路人踏为平地。父亲告诉我:“针孔可以成像”。这消息使我欣喜若狂,我整天拿着一个扎了针孔的纸盒子对着窗户,看纸盒里的“成像”。针孔换成了放大镜,却制造不出快门,像机还是没有做成。我找来一个木盒子,一堆马粪纸,收集父亲的老花眼镜镜片和母亲的显微镜镜头,用九分钱一把的铅笔刀为工具,折腾了好些大,做出一只望远镜和一台放大机来。望远镜可清楚地看到院墙上土钵中的仙人球刺,放大机能将底片上指头尖大小的面积放大,实验的成功使我兴奋了好久。我恳求父亲给我买一台照相机,但那时家中姊妹多,经济条件不许可,这愿望终没能实现。日后我也没有专门从事摄影,但20年后,我依然喜欢在暗室里折腾,想来却与儿时相关。
父亲希望我在他的身边读他的“大学”:物理学,但我最终还是迷上了绘画。1977年的恢复高考,给了我上大学的首次机会,阴错阳差,我放弃了四川美术学院到北京就学,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设计专业的四年本科毕业之后,我被留校任教。迷恋绘画并充满了创造欲望的我,因涉事太浅,长久地不知道该怎么努力。后来,我去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做美编,中国美术报做执行编辑……
命运象在捉弄我。我的油画《流》在大学二年级时(1980)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的铜奖,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它;以后又以连环画、油画、版画和丙希画等参加过全国美展和市美展。但在大学期间,我创作得最多的却是诗歌。我从不知道它们可以发表,一些人看了说喜欢,拿走了。它们有的被发表了,有的没有了下落。出于工作的职责,我做过电视剧的美术设计,参加学院的教学和演出的配合工作;我画插图,搞封面装帧和海报广告设计;写美术评论、报道和采访……但我心目中最高的艺术追求仍然是油画。西藏归来,我发表了一些油画和诗歌,但发表得最多的却又是摄影。如此地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之疑,惹得一些好心的同行师辈和朋友的惊咋和善言相劝。
对油画,我曾以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而我越是追求于此,它就越是显示出它的高度和难度,不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与艺术的追求,油画便象是久孕的奇胎在我生命的底层膨胀。它形成得早而容易,却成熟得晚,不到成熟,它好象不能诞生。
人讲顺从天意。我终相信,凭着对生命与艺术的虔诚和苦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我生命的过程中不可抗拒的种种劳动的方式,我都一视同仁的认真。摄影是我一种获取外部世界种种形象和材料的方法,暗室里的工作是一种乐趣,我爱油画则为人生,在绘画表现所不及的领域里,我觉得文字对我充满了魅力。
而我从小就体弱,病魔就象咬上了我,让我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环境中品尝各种疾病之苦。也许因为体弱,我才特别渴望到自然中去展示自己的力量;也许因为我不具备强壮的体格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这种展示,我才在艺术里发现了更含蓄而永恒的力量。
第一次独自远行是1985年去云南写生,我到了瑞丽的弄岛。我的主要收获是相信了自己独立的力量,它为两年后我独自去西藏奠定了基础。西藏成全了我生命力量的最大张扬,也破坏了我最为纯静的生命幻觉;多次往返高原、不辞辛劳的工作也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数年之后,我才从一种新的形式中艰难地找回自己的力量,于是有了《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这本书。
1992年6月于北京
--------------------------------------------------------------------------------
背景:
寻找青鸟(作者自序)/巴荒
作为一个东方的女性,我从事艺术,关注生命与自然之种种相互关系,像所有的“痴人”一样探索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追求“文明”而又渴望“回归”,却既无法摆脱文化亦无法摆脱非文化的存在;无法摆脱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失落;亦无法摆脱追求更高层次文化与宗教及生命的渴求所产生的困惑——生命的核心是一座巨大的荒原,而西部的自然反射着生命的奇观……
许多年过去了,无论世上发生何种变故,我始终不能忘掉那些时光,也不能忘掉那些东西。一它们究竟是什么?我想,使我不能遗忘的东西,一定是生命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人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或被寻找着什么,它可能仅仅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状态。它有时附在一事一物,有时却游离在不知方位的虚空。我曾总是固执地寻找和等待,幻想它在某一具体的物或事物上完整而永恒地托现,并在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苦苦地搜索……经历了彷徨、失望和离奇的艰辛,我终于一次次发现了它,它却一直就与我同在——那就是这种与原始自然和它派生出来的情感割不断的神秘联系和独特的理解。人生也罢,艺术也罢,对我来说,一切动力和创造热情皆源于此。因此,才有了我数次独行西藏阿里的冒险生涯。
我想以我对自然、对一切生命体和对艺术强烈的爱,以我生命的体验并努力超越个体生命意义的视觉,来再现和赞颂西藏独具魅力的、带有象征意义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而它言未尽,言不能尽。
但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人们发现,青鸟就在我们自己的肩上。
(巴荒 1989.12)
--------------------------------------------------------------------------------
请读片断:
西藏摄影选一
…………………………………………………………………………………………
无人区:通往阿里
(片段) 巴 荒
我要去阿里。
由拉萨到阿里地区政府所在地的狮泉河要途经藏北“阿里无人区”,1764公里的路程没有交通车,只能求人在拉萨的阿里办事处找运送物资或人进阿卫的车辆,搭上车的机会却很少。没有闲人进往阿里,即使是得天独厚在拉萨工作的美术同行们,去过阿里的人也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女人无伴独行。
羊桌雍湖
位于藏南浪卡子县境内,海拔44000米
每年阳历六月的
跳步扎(打鬼挑神活动)
我要一人进阿里。提及阿里,聚集在西藏大学的同行及熟人们竟谈虎色变,争相向我提供荒凉绝伦、风险离奇的传闻,原来自告奋勇要陪我前往的朋友也退了。似乎我今生此去就难返回。而进阿卫这个久久潜入我心内的强烈愿望已势不可挡。我觉得西部荒野的大自然,潜藏着我最隐秘的生命之源,一种秘密的呼唤正等着我去回答和验证些什么。1987年6月29日便悄悄地载入了个人的史册。
告别拉萨时,我又兴奋又忧郁,好像在与我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告别。尽管我幸运地搭上了去阿里的车,并且还是号称“巡洋舰”的越野车,启程后约100公里的路途中,我都神不守舍。直到车离开北面逆向奔流的雅鲁藏布江,驶上海拔4790米的岗巴拉山口,我才从冥想中拔足,同车内的藏人们一起呼喊:“嗦嗦罗——”。
两位藏族妇女要下车给山口的摩尼堆献哈达,车子正好停在俯视“圣湖”羊卓雍错的山道旁。我第一次看见西藏的高山湖泊,就是这座喜玛拉雅山北坡湖盆苇中最大的淡水湖(约800平方公里)。从高出湖面几百米的山口眺望,它确如镶嵌在群峰之中的蓝宝石,那种纯粹的色彩和宁静感以及湖畔的水草、牛羊马群、密集的白色水鸟所带来的悠悠生息,使人如此的赏心悦目,至今我仍认为羊卓雍错是西藏最俊美的湖泊。
去阿里的路沿羊卓雍错行,经过浪卡子进入日喀则的江孜地区,远远就看见江孜宗山上的旧城堡垒。而宗山下的白居寺,我在一年之后才得以有机会一览寺中白居塔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我们的车子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市仅作了极短暂的停留,我也只能随车经过座落在城西日光山南侧占地13万平方米的札寺伦布寺,遗憾地在355公里桩的地方告别日喀则市。但我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我竟作为日喀则地区师范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员,就在离这块界往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开始了我的援藏生活,并常常往返于札寺宫墙外随山势迤逦的转经道,以后又多次从这块界桩脚下经过,去纳唐、萨迦和定结,去定日、聂拉木和樟木,并再次经过这儿去阿里……
车行151公里的路程之后,在拉孜渡口与东去的雅鲁藏布江重逢。由东往西的车辆都得在此等候浮船过渡。车子从南岸到北岸后就在江边的阿卫物资转运站落脚过夜。为了赶路,我们的车子第二天凌晨四点天不亮就出发了。司机是个汉话说得不错的藏族青年,但车中的闲谈,仍是藏语为主,一车六个人,只有我是第一次涉足阿里的外来客,每公里的路程对我都是未知而孤独的,这倒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领会黑夜和白天里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一切。车子离开拉孜渡口200多公里之后,已临近中午,有人说:“马上就到二十二道班了!”说到二十二道班,车中的人们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兴奋。我是第二年从日喀则搭上由青海开往阿里盐湖的车队再次进出阿里时,才体会出二十二道班独特的亲切感的。那次结伴同行的四辆东风牌卡车,在二十二道班地处荒野的破墙围子露宿。全车队六个司机和一名机修工没有一人进过阿里,我便成为车队精神上的向导,在司机台中度过的夜里首先饱尝了二十二道班所给予的精神鼓舞。这个地属日喀则却由阿里行署所设的驿站在阿里荒原与日喀则乡野的汇合处,它是人们走进阿里荒原和走出阿里荒原的一种象征。
而真正的阿里荒原(泛称无人区)是从拉孜起数的234公里桩后的岔口伊始的。车子行至此,正如音乐曲调一转,爵士乐接古典乐,在一块插入泥土的铁牌处——生锈的铁牌上白色的手体藏汉文写着:向前:仲巴203公里;向右:措勤236公里——离开车道往右边翻浆的干泥坑地“哐啷”、“哐啷”,我激奋的心也随着它的“哐啷”声开进雨洪侵蚀后又被太阳蒸干的荒滩,开进无垠的阿里高原,就像一只小舟驶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无人区丧生的牦牛尸骨
阿里,阿里。我终于跨进了地球上高高隆起的这块36万平方公卫的土地,在东经78°30′00″至82°00′10″、北纬30°00′00″至34°20′00″之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阿里藏北高原之上,在脚下这片向西北延伸,一直到新疆昆仑、到青海可可西里的20万平方公里藏北无人区之中……。而关于阿里,我在踏入这块神秘区域之前对它的了解甚少。我读过一则关于阿里札达古格王朝遗址的考察报告,一张随文图片把一座依山叠起的风化古堡深深地印记在我脑里,“阿里”这个地名才第一次跃入我的心中并和西藏有所联系,但札达离此地还太远;有关西藏的书都告诉我关于岗底斯“神山”和玛法木错“圣湖”的故事,它们也发生在阿里,而“神山”、“圣湖”离此处还太远太远。我读过海因利希·哈雷的游记《西藏奇遇》,这位当年德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员,奥林匹克的滑雪冠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印度的英军扣押的战俘,曾在西藏生活了7年之久的14世达赖的老师、旧时噶厦政府的官员,通过他从阿里边境逃入西藏避难的艰险历程和他顽强卓绝的生命意志,使我初次触摸到阿里历史中的生息和原始中的自然;我还曾读过一篇涉及到青藏高原的小说,它总使我联想起“母亲”这个亲切的词汇,它把高原自然中野性的粗矿、苍劲甚至忧伤像梦一样一并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让我一触及到“原始自然”这几个字,一种喜悦,一种渴求就涌上心头……我感觉到一种与自然的独特缘份。阿里这条最颠簸、最荒凉的陌生之路竟让我觉得这么熟悉这么真切,一跨进这片广袤就有一种回故乡的感觉。
不知道究竟是在梦中常常与它相逢,还是我的始祖把生命之初水乳交融的泥土气息和它独特的影像,通过不为人知的信息传递储藏到我体内的冥冥深处,使我就生活在其中,吮吸它慷慨馈赠的甘露,栖息在它铺满阳光的温床上;我在它广博的胸膛自由驰骋,象荒原中的任何一只野生动物,也象寻找金子的第一个孤独的开矿人,在它最苦涩、最贫脊的寂寞深处行走和敲打……
的确,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再也没有比通往阿里这种骤然阳雪骤然阴雨又被太阳蒸于、这种既寂寞荒凉又生态悠然的风尘之途更令人亢奋而亲切的路了。离开二十二道班的岔口穿越阿里东三县的1000余公里路途中,时儿沟壑时儿又平滑如鱼脊的野坡,时儿无穷无尽起伏的荒滩时儿又一马平川的草原,到处散落着灵性的石头或风干的动物尸骨,到处仁立着透迄而冷峻的高山,横卧着平静而幽深莫测的湖泊。
无人区途中的
荒凉而充满灵性的野石滩
沿着干沙石坡展开的
摩尼石堆和经幡旗
在天还未启明地还未解冻的凌晨,赶路的车灯射出两道雪亮而让人感觉冰冷的光柱,引起散布在山岗土道的野兔阵阵惊惶;等太阳把夜寒驱散,成千上万只忙忙碌碌的土拨鼠在铸成蜂房般的泥疙瘩土原上,一丝不苟地窜上跳下,在开裂的土堆上来回穿梭,好像要把整个大地都认认真真地翻上一遍;而正午,在池边沼泽地里养息的旱獭,在水中嘻戏的黄鸭、丹顶鹤与白色的水鸟缓缓地扬起悠闲自在的头;还有在原上成双成三驻足窥视的黄羊,它们或角逐汽车,或调情似的奔向隐蔽的野岗;有时,一只独狼在深沟隔断的对岸高台观望,像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调头悄然消失于远处的山脊;有时,一只孤雀在茫茫原上飞行,落在一根偶然出现并早已枯死的麻柳枝头,摇摇晃晃象个疲惫的流浪儿,不知道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何处又是它躲蔽风寒的巢穴;而喜欢在盐湖边成群狂奔的野马(当地人称野驴),扬起烟幕般的尘土犹如古战场冲锋陷阵的军队,并且总会有两名“勇士”冲出阵地和偶尔来到高原的汽车赛跑。它们扬蹄向还相距几百米远的汽车靠拢,直到和汽车并肩相距不足3米,急促而洪亮的蹄声压过汽车马达的轰鸣。这时的草原真象一面紧绷绷的战鼓,蹄落地面敲出饱满的“催战”鼓点,把整个草原敲得激奋而壮烈。它们还在继续向汽车靠近,一米、半米……眼看着它们就要和车头相撞,犹如一场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已不可避免,然而它们总是奇迹般地冲撞,扬起马鬃恰似斗牛士扬起的披风对准牛头而与奔驰的汽车相切,然后与地面形成60°斜角的四蹄和身躯在阔大的草原上划一个巨形的弧,才在遥远的山麓收兵歇息……司机告诉我,曾经有与汽车角逐的黄羊,超过汽车之后就因心脏破裂而死。何等的英雄气概!自然界中的动物不仅仅是为生存而竟争,也为荣誉和尊严而竟争。而黄羊之死则并不为领取奖赏,它死得那么痛快、单纯!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动物所具有的修养和品格,而使我们人类少一些自诩。吃人的狼曾养活过人,而创造文明的人类却制造了无数的战争和死亡。人类战争的阴云还在地球上蔓延,但战争能够避免吗?它似乎成为人类自我完善中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如果你一口气把人类的历史读完,你就会感觉到人类的包袱太沉重了,正象眼前纵横的山包,压在高原的胸脯上不能摘除。
生活在盐湖的藏族的家庭
藏北阿里宽阔的高原平台有时能延续数10公里,远看象一块块铺向天边的灰绒毯,近看却是碎石滩,草茬低矮稀疏而枯黄。阳光下的大地成为一个整体,数百米之外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动物的警觉;而如果在远处的山麓或草原上有一个小小的斑点与散落在草茬间的碎石不一样,我就准能等来期待中的生命出现,但有时这种渐渐扩大的游动斑点又渐渐缩小,还没传来蹄声就消失了。
草原的大地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它根据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时辰甚至是不同的构成形态,对驶来的汽车发出不同韵味的颤音。但有时,车子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丘,开进一片又一片高原平台,除了风。除了阳光和车自身,什么动静也没有,大地的声音连同它被太阳晒败了色的身躯一样单纯一样苍白。无论我是向左右看或是向前后看,永远是重复移动的线条,重复移动的色块和重复流转的声音。即使我闭上眼睛,那些重复的色块和线条的影子,仍在我的视觉残像里一片片涌现或一片片退却。时间一长,我竟觉得自已变成了这无穷无尽的山峦和沙石滩,而这如铁瓢虫一样爬行的汽车正在我的太阳穴上反反复复地压出无数条交叉重叠的车辙,正好像一条条交错而织成网状发展的哲学思路那么具有发光的诱惑却又让人疲惫不堪。有时,在坑洼不平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一具马尸或牛尸,那形象真好似一个被现实打败了的哲人,却风度翩翩地等待狼、等待老鹰和乌鸦来啃啄它的身躯,等待真理永恒的最终显现……
--------------------------------------------------------------------------------
目录:
找青鸟(序)
无标题摄影作品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日光城
雅隆河谷寻古
无人区·通往阿里
普兰·冈底斯的引力
札达遗梦
古格日记
走出荒原
附录
巴荒进藏路线图
自述
巴荒油画作品
后记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