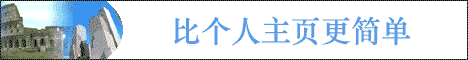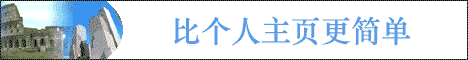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
|
|
程泰宁对张在元案的一封信
ABBS
|
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的这篇文章无法登上内地网站,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了我,我想这绝不应该是文章内容的原因。因此我想借代薛教授发这篇文章的机会,也写几句话。
我完全赞同薛教授对张在元先生在专业上所表现的来的出众才华的评价,当我每次翻阅张在元教授的“天地之间” 、“非建筑”这两本书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震撼。我搞了一辈子建筑,我以为,把绘画和建筑创意结合起来作图,就其想象力和表现方式而言,无论国内外,我还没有看到比这更出色的。至于张在元教授为中国建筑界以及“武大”所做的贡献,薛求理教授的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遗憾的是,自媒体曝出张教授被解聘的消息后,由于对事实不同的判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觉得目前的这种争论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于事无补,并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非常赞同薛求理教授对此事所持的态度:
1、重要的是要了解并介绍张在元教授多年来的工作成果和贡献,以及他敬业、创新、拼搏的精神,在当前,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为张教授治病、生活进行捐款,在我们建筑界提倡一种相互关心的风气。我也希望这件事能有一个组织站出来牵头。
程泰宁
附薛求理原文: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为张在元先生祈祷
薛求理
近日,内地不少网站刊出新闻标题《武大解聘病危教授》。那晚,我好奇点入新闻,赫然发现张在元先生的名字!张在元先生,病危,解聘……这些字句和这位强人汉子联系在一起? 我看着报道,不禁感到心和手都在颤抖。
张在元先生是1980年代中国建筑界的英雄,80年代建筑系毕业生鲜有不知其名的。1980年,青年教师张先生在武汉城建学院任教,他的设计‘长江水晶宫’在日本新建筑杂志社举办的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在此之前,曾有西北设计院的曹希曾先生在日本获奖。那年头,要把建筑设计图寄到外国,可是要大学或局一级的介绍信,邮局方肯受理。张先生的设计一发而不可收,一共获得17次奖,其中包括1987年度日本新建筑杂志社竞赛的一等奖,而受到出题人楨文彦先生的接见。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奖多是杂志社举办,现在很多学生都能获奖。但在改革开放的初年,这些奖项,给正跃跃欲试的中国建筑界很多的启发和鼓舞。1988年,世界建筑杂志社在成都举行‘走向世界’研讨会,与会的近三十位设计竞赛获奖者无疑都是那个年头的皎皎者。
1984年,张先生向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建议设立建筑系,他成了武大建筑系的创办人。因着楨文彦先生的看重,张先生于1988年赴东京大学,此时已经37岁。到了东京时,恰逢日本东京国际论坛举办设计竞赛,中国建筑师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国际设计竞赛,北京的马国馨团队和上海的戴复东团队都有参与竞投。张在元先生协助国内的设计团队,在东京修补模型。这次竞赛,美国纽约的Vinoly事务所获得第一名,该大型项目于1994年在东京市中心建成。张先生将这次竞赛的见闻详细地写出来,揭示中国设计院和国际事务所的差距,此文发表在北京的建筑学报上。
1980年代,中国建筑界刚刚从极左思潮的紧箍咒里走出来,建筑创作方兴未艾。一群中青年建筑师热情高涨,成立‘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刘开济、罗小未、艾定增、曾昭奋、吴国力、张在元、程泰宁、邢同和、李大夏、罗德启、饶维纯等等(这批人士21世纪成为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WACA的主力)。有感于中国建筑师的地位不如人意,北京建筑师丛刊在当时开辟‘新中国著名建筑师’专栏。曾昭奋和张在元先生主编了‘中国当代建筑师’一书,第一集由天津科技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到1992年一共出了4本。这类书现在多到泛滥,但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出版突出个人设计的书,还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些书籍和文章高扬了建筑师的业绩和设计的重要性。
张在元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上海、香港、横滨在19世纪20世纪初开埠时的比较研究。这个选题独辟蹊径,看重了这三个东亚城市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同路径。殖民时期的水边建筑,香港已经荡然无存,而上海和横滨却是有迹可寻。这里面确是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高质量的中文英文出版物几乎没有。在研读博士期间,张先生在国内频发文章,他的文章多从全球化眼光,看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也出了几本书,介绍楨文彦的作品和日本的现代建筑。这些作品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建筑学界无疑有重大影响。1995年,张在元获得东京大学工学博士。他在香港‘建筑与都市’杂志撰文,引用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二战结束时的演讲,汗水、泪水、血水交织。
张在元先生从1990年代起研究香港城市,1997-98年任香港大学研究员。1998年,张在元和刘少瑜合著的‘香港中环城市形象’,由香港贝思出版公司出版。 张先生的钢笔素描,将香港中区的殖民建筑和大榕树描绘得出神入化,那大片的树叶和阴影,不知是如何一笔笔画出来的。贝思公司老板林先生说,张在元的画,捧在手里,都不忍放下。张先生关于香港城市的类似文章,发表在北京建筑学报和香港建筑师学报上。2003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在元的著作‘天地之间’,其中收录了大量画作。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对张先生作了专题报道。
在香港工作的前后,张在元赴美国加州考察。之后,他在广州规划设计了‘国际生物岛’。1999年,‘生物岛’的图纸和模型在广州的大型国际招商会议展览,它的大胆设想和概念让与会者震惊,它对国内以后的类似开发有很大的引领和启发。后来,张的团队在合肥也设计了类似的项目。据我印象,广州‘生物岛’直到2009年,还未完全建成,而迟起步的大学城却在2006年就收生开学了。广州市政府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生物岛的建设,实施方案和张在元的构思相距不远。广州生物岛后,张在元在广州成立喜马拉雅工作小组,做了许多规划和建筑设计,记得一度还出版杂志。2005年,张在元重返武大,任城市设计学院院长。说他是武汉大学的功勋教授,大概是一点不为过的。
张先生对中国建筑界的主要贡献,在1980和90年代,他的设计构思天马行空,文笔激情洋溢,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呐喊。他参加的设计竞赛,对中国建筑界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读张先生的书籍、文章和画作,钦佩他的才华之余,常常惊叹他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那么多的事。50来岁,正当壮年,设计研究教学一把抓,朋辈在盼望着他的新作品和文章;多少莘莘学子嗷嗷待哺,等待张院长的教诲,他却无端染上顽疾,一病不起。出师未捷,泪已满襟,闻之令人心碎。我相信,张在元的病,是长期积劳成疾出来的。他太辛苦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披荆斩棘,一路奔走过来。
著名建筑师在大学任全职兼职、终身制合同制,教授院长,本是世界惯例。对大学来讲,求之不得,好处不言而喻。对建筑师来讲,会比较奔波劳累,但搞得好也是名利双收,对学术和设计各有推进,如Rem Koolhaas 和 Steven Holl就是最好的榜样。我读网站上的报道,张在元先生和武汉大学签的是4年合约。这样的合约,自然完结,到期不续。本来是不需要什么‘宣判’的。大学方面竟然派了四个单位的人员,到病床前向神志清醒、但却不能言语的张先生‘宣判’,实在是无情无义,丧尽天良。建筑学本来就是累人的活,这样的体制不改变,会有更多的张在元倒下不起。正如许多网友所言,张在元尚且如此,那更多奋战第一线的中青年建筑师岂不更加困难。
我吁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学会湖北分会和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出面关怀张在元先生的境遇,在会员和协会网络中进行筹款,支持张先生医病。海外的专业协会,每年交会费,都有一定的数额拨入‘会员善款’(此一部分有时也以自愿捐款形式,数额尊便),供会员在突发事件时互助。衷心希望奇迹发生,张在元先生可以身体康复,重新站立起来。遥望北天,心香一炷。
·发表评论 |
|
[更多评论]
[更多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