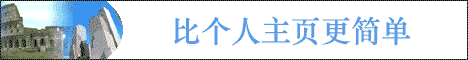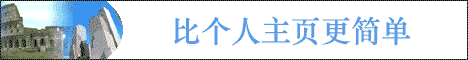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
|
|
城市建筑乌托邦
沈克宁
|
【摘要】城市和建筑乌托邦将建筑和城市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实验场。20世纪的现代城市最能表现现代技术的力量和美学观念,它也表达了一种执行社会正义的进步思想。这时期的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们相信并且展望一种城市的革命性的重建不仅可以解决该时代的都市危机,而且能够解决社会危机。乌托邦是历史上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理想”城市建筑和社会。乌托邦也是人类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可以忽略自然条件的限制去创造完善理想的城市和社会。本文探讨了现代主义以来城市建筑中的乌托邦实验,尤其是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未来主义城市建筑、构成主义的理想革命社会、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赖特的广亩城、阿基格拉姆的技术社会、情景主义的偶然和暂时性社会、索托萨斯的反现代主义、库哈斯的发狂的纽约和伍兹的新世界。
【关键词】乌托邦 理想城市建筑 霍华德 花园城市 未来主义 构成主义 明日的城市 广亩城 阿基格拉姆派 情景主义 索托萨斯 库哈斯 伍兹
Abstract: Behind the Urban and architecture utopias lies the utopian spirit. The spirit is the felling that society is capable of improvement and can be made over to realize a rational ideal. Utopias were inspired by the prospect that a rad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ies would solve not only the urban crisis of their time, but the social crisis as well. These ideal cities are the most ambitious statements of utopians believe that reform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can revolutionized the whole life of a society. Utopians considered design as an active force, distributing the benefits of the Machine Age and Post-industrial Era to everybody and directing the society and community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Utopia; Ideal city and architecture; Garden City; Futurism; Constructivism; Radiant City; Broadacre City; Archigram; Situationism; Ettrore Sottsas; Rem Koolhhas, Lebbeus Woods.
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由于与人类的社会和生活紧密相关,因此通常与社会改良思潮和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改造又经常是通过物质环境的改造开始和达成的,所以建筑和城市改造便成为热心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们的实验场。社会改造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城市改造,社会改造的实验场通常是在更为具体的物质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改良者借助物质环境的改造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在传统社会中,人造环境具体地体现了社会制度,人造环境的形式、格局和制度不仅反映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制度,而且起到执行和强化这种社会制度的作用。各种社会,如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建筑都表现出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激进思想的建筑师、城市主义和社会改造者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去创造一种自由和开放的人造环境。
城市和建筑乌托邦将建筑和城市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实验场,在这样的实验场中,建筑和城市被认作是表现“意义”的场所。建筑和城市无疑具有意义,而且是一种具体的、物质的社会改造工具。它不仅要表现某种意义,而且要执行和强化这种“意义”或“秩序”。乌托邦是历史上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理想”城市建筑和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人类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可以忽略自然条件的限制去创造完善理想的城市和社会。
社会激荡的时代通常也是城市和建筑领域出现大胆、激烈、创新和变革式的理论和实验性尝试的时代,具有产生新思想、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土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大革命前出现的构成主义理论和实践,1960年代意大利学生运动期间的新理性主义有关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的讨论都是典型代表。新思想、新理论和实践的极端表现便是城市和建筑乌托邦。城市建筑领域乌托邦思想和理论的典型代表有20世纪初英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20-30年代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40年代赖特的“广亩城”,60年代英国建筑电信团的“行走城市”、“插座城市”,70年代库哈斯等人针对曼哈顿所进行的一系列乌托邦作品,以及近来美国建筑师利布斯·伍茨(L. Woods)的一系列新城市和建筑作品。20世纪的现代城市最能表现现代技术的力量和美学观念,它也表达了一种执行社会正义的进步思想。这时期的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们相信并且展望一种城市的革命性的重建不仅可以解决该时代的都市危机,而且能够解决社会危机。
1.乌托邦与城市建筑
自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有乡》(Utopia)在1516年出版以来,它便成为文学领域乌托邦的原型。当然,更早的乌托邦体现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一书中。城市方案和设想领域的乌托邦虽然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原型不太相同,但乌托邦的精神尚在,属于更为广泛的乌托邦范畴。20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作为被统治势力的权力系统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作为反对派的乌托邦之间作了区别。他引进了如下的概念,那就是前者是固定、停滞、被动和反应式的,后者是能动和进步的[1]。在城市和建筑乌托邦领域这种界限有时是不很清晰的。在某些情况下,设计者所提出的建成环境是试图强化一种现有的权力结构,这是一种社会理想化。在另一些情况下,设计和提倡一种良性的物理环境是为了带来社会变化,这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因此城市和建筑乌托邦所提供的最佳城市框架就要么是反映了最好的社会秩序和安排,要么是引进一种可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毫无疑问乌托邦和理想城市的幻想者们大多属于精英阶层,他们之中最早的要数柏拉图。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最有资格将人类社会纳入宇宙的秩序,从而在混乱和混饨中建立和谐与秩序。莫尔自称他想像的乌托邦是对柏拉图所梦想的共和国的一种具体化,从而实现了柏拉图的梦想。这种哲学家执掌社会的观点直到17世纪早期,在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阳光城》(City of Sun)中仍然占有地位。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筑师便试图将该重任从哲学家手中承接下来。 赫兹拉(Joyce Oramel Hertzler) 在他的《乌托邦思想之历史》一书中将莫尔、培根、坎帕内拉和哈林顿等启蒙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称之为“早期现代乌托邦”[2]。早期现代乌托邦的思想在现代和当代城市建筑乌托邦实践中得到了延续。
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乌托邦越来越变得具有可行性,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后19世纪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俄国和德国,都有一些乌托邦出现。圣西蒙、傅立叶、布兰克、欧文等一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所进行的小规模社会实验通常都是短命的。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开始对乌托邦的手段和其所要获得的结果进行质疑。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反乌托邦作品。这种反乌托邦式社会其实自身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所想像的世界是一种非理想化的地方,一个悲惨世界。
1898年霍华德发表了有关“花园城市”的著作,1902年经过重新编辑成为《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3] 一书。 霍华德具有革命精神,他原初的构想是将花园城市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他试图用花园城市去创造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他严格地勾画出新城市规划发展方向以及先进的实践手段。这包括各种城市规划的问题:土地使用、设计、交通、住宅和财政等等。他还将所有这些思想编织进一个更大的组织系统中,那就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的社会,以及获得这种社会所需要的纲要[4]。霍华德这个出现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思想,是建立在传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经验之上,而对20世纪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在花园城市中,他明确地表明希望通过物质环境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他深信他同时代的19世纪城市现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要么使得极少数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永久化,要么导致激烈的阶级对抗。他认为重新组织物理环境将会为社会进化到更为文明的阶段提供一个框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表现在“三磁铁”的图示中,在这个模式中人们为两种现存的物理环境:城市和乡村,以及与这两种环境相对的,被他称之为“城-乡”的第三种新环境所吸引。对他来说城乡结合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和乡村所具有的健康和充分空间的生活环境。他设想一系列由这样可容纳3万人口的城镇组合成的集团互相联系,同时以更大的可居住5.8万人的城市构成城市中心。城镇和城市之间由快速交通系统联系起来,由此组成了多样和令人激动的“社会城市”。他设想在城市中心布置的是有助于公共娱乐和市政活动的建筑,中心公园包括市政厅、图书馆、展览馆、医院、音乐厅和讲演厅。小型市场、居住和工厂位于城市的边缘。他特别强调每个城市一定要有不同的特色,从而与托马斯·莫尔的那种单一形式的城镇形成了区别。
现代主义运动以前的乌托邦,不管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有多么美丽,都显示出很浓重的极权主义倾向。霍华德是现代主义运动初期第一位试图修正这种极权主义倾向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明日的花园城市》试图纠正对他影响很大的、于1888年出版的贝拉米(Howard Bellamy)的小说‘Looking Back’中的极权主义偏见。霍华德试图在“花园城市”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中创造一种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力和创造之间的恰当平衡。他的“花园城市”理论在20世纪以来激发了无数花园城市式的城市实践。
2.乌托邦与乌托邦城市特征
乌托邦有两种表现形式,着眼于过去和着眼于未来。强调第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们”通常是那些向后看的人们,他们试图在过去中拾回失去的往昔和逝去的黄金和理想时代。他们极度地想要回到过去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发现自己,重新体验那种归乡、回到家园的平静感觉。目前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充满了缺陷,未来则是不确定的、对社会充满了危险。他们总是对变化充满了恐惧感。对他们来说曾经尝试过的,并且被证明是可行的模式提供了安全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他们认为过去是理想和完美的。展望未来的乌托邦则是向前看的,他们企盼未来的更为理想的社会。这些乌托邦的畅想者们通常是时代的先行者,是独立的思考者。他们具有独立的思考精神,是先驱者。他们为人类构想了可能的更美好的未来和更完美的幸福,用以取代目前社会和道德的缺陷。他们藐视传统,抛弃理论和政治的偏见,从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相脱离。他们是持异议者,是反对派,是社会的对立面,是极端的少数。他们拒绝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中毫无声息地消亡,他们也拒绝保持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他们是自由主义者,是美好未来的倡导者,他们不害怕社会的改变。虽然他们是社会的极少数,但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事实并不为大众所接受和支持。因为乌托邦很自然地也是他们本时代的批评者,他们向人们展示了目前的现状与未来可能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乌托邦主义者们毫无例外地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具有原创性的思考能力和创造性的想像力。
伊顿(Ruth Eaton)的《理想城市》(Ideal City,2003)总结了乌托邦世界的特征:首先它必须是不借助非自然之力,通过人力来试图获得的乌托邦环境。通常这种世界是由那些面对动荡社会的现实,感到无助又无能为力的人们所创造的。乌托邦的创造者通常希望他们的设想能够实现,因此通常他们试图与统治者相沟通。乌托邦通常是作为取代被认为是混乱的现存状态的一种替代物。乌托邦的志向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社会重建或科学进步而取得更大的集体幸福与和谐。乌托邦通常表现在城市上,这种城市通常是用几何线规划的,它意味着用人类的理想来统治自然界混乱的力量。乌托邦通常是以绝对的答案来表现的,它被认为是可以施加在世界各地。对于乌托邦来说,地区特征和内涵,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都没有什么区别。乌托邦通常又是在处女地上建造的,而且没有为未来的变化留有任何余地。乌托邦城市和社会与外界的隔绝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要么在图中用自然的屏障如河流和延艮的山脉,要么用人造屏障如城堡、城墙和绿带来隔离。当然这种隔绝同时具有物理性质和象征性质。隔绝不仅表现在空间上,它也表现在时间上,乌托邦社会和城市明显地试图与过去和历史相分离。又由于乌托邦自认是理想和完美的,由此它并没有为未来进行修改留有余地。它的目标是对理想完美的乌托邦进行复制。莫尔的《乌有乡》中在与世隔绝的土地中的54个几乎相同的城镇便是典型,莫尔试图用这种相同的城市平面来适应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同时试图消除人们不同的个性。因为乌托邦强调集体性,认为个人的兴趣和愿望与集体愿望是完全和谐的。多样化、个性、兼容性等民主的最基本要素在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模式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现代的工业化的进程也助长了这种标准化的梦想。这种标准、工业化的城市和社会理想在现代主义的城市和建筑中成为主导力量而具体和实践化了,经典乌托邦城市规划的代表是柯布西耶的乌托邦经典“明日的城市”。
3.20世纪前半叶的城市建筑乌托邦
伊顿的《理想城市》一书对历史上和当代城市乌托邦的典型代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将这些乌托邦活动总结为对“理想城市”的追求。该书有关现代主义阶段乌托邦城市建筑的探索十分系统和完整。下面对他的研究进行一些介绍。
本世纪初技术发展的突破、大都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和德国革命,都给人以新世纪即将出现的警示。这是早期的、英雄式年代。法国的圣-西蒙认为组织化的工业将会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基础,这个世界由工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工业精英来管理。这种思想对想要治理世界的建筑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无论是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的世界,还是赖特的“广亩城”都需要一个有绝对权力和公正智慧的建筑师或规划师来管理。对柯布西耶来说,为了集体的利益,他的任务就是构想一个“彻底的、完全、公正、无私和无可争议的系统”[5]。这些都显示那是一个产生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时代,现代建筑、国际风格以及为了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而将新的生产和营建方法结合起来的雄心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张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表现主义同时出现了一批乌托邦的畅想者,如哈里克(Wenzel Hablik)就绘制了一系列漂浮建筑和飞行城市。1928年希伯尔姆(Ludwig Hilberseiver)负责包豪斯的城市设计,他将他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有关理想城市的设想概念付诸于柏林城市设计中。但是围绕包豪斯由表现主义和功能主义者设想的有关纯粹的、崭新的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很快就被纳粹所粉碎。
伊顿认为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对城市和建筑乌托邦的贡献也很大,未来主义崇尚速度“我们确信伟大的世界被一种新的美所丰富,这种美就是速度之美……今天我们靠速度来建立起未来主义,因为我们要将这片土地从臭气熏天的教授、考古学家、古董商们的手中解放出来……拿起你的斧头和锤子对这个可怜的城市进行无情的打击”。[6] 这就是马里内第的未来主义宣言。该宣言在城市建筑中引进了第四个向量:时间/速度。这是对理想和乌托邦设计的一个重要贡献——时空概念。虽然未来主义在其本土有着丰富的遗产,但他们对新出现的城市并不满意。他们声称每个时代都应该拆除旧有的城市,建造该时代自己的新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未来主义有关重建世界的思想重新由马奇(V Marchi)和法尼(V Fani)拾起。1914年建筑师圣-埃利(Sant' Elia)加入未来主义。他在1914年的展览中有关“新城”的绘画作品表现出他的理想城市思想。他认为重新创造建筑可以最为准确地表现人类目前世界的机械状态和本质。他的环境是有关技术和动态/感的。他提议拆除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建造一种纪念式的、多层次的、没有装饰的城市。他的城市由钢铁、玻璃和混凝土构成,其主要特征是外部电梯、扶梯和火车站。他说:“未来主义建筑所提出的问题是关注未来主义住宅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关于使用所有的科学技术进行营建,满足人们习惯和精神的需要,决定新形式、新线条、轮廓和体量的新的和谐性。一座建筑存在的原因仅可以从现代生活的独特条件中,以及对人们感知的审美价值的反应中发现。这种建筑不能被任何历史延续性的规律所束缚,它必须是崭新的,犹如我们全新的思想状态。”[7]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在旧制度下感到孤单和隔绝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展开怀抱迎接革命,准备将自己的思想、知识和热情投入到刚刚诞生的新生活中。先锋派艺术家在1917年走上街头,参加了革命。他们自认可以融入充满生气的新生活中,而艺术将重新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艺术家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自认可以在社会中所起到更大作用的革命中的时刻,建筑师则认为他们的实践领域将远远超出仅仅为雇主设计和建造物质环境上。他们积极地拥抱整个新兴的社会并通过建筑和城市结构去组织革命的召唤。这种对革命和新政府的热情可以从维斯宁(A.A and V. A. vesnin)兄弟的言论中表现出来:“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开始了,任何阻碍新生活发展的力量都将被革命的巨大洪流所扫除。建筑师面临通过对现实进行反映并组织新的生活进程而跟上或满足作为新生活建造者的任务的挑战。”[8]
塔特林(Tatlin)等人的构成主义,马拉维奇(K. Malevich)等人的至上主义和拉多夫斯基(Ladovski)等人的理性主义虽然在革命前就已经产生根基,但在革命后前几年的乌托邦热情中得到极大的发展,直到1932年斯大林终止了所有这些实践为止。在1917年后的几年内,在苏维埃乌托邦作品层出不穷。列宁自己受到坎帕内拉《阳光城》的影响而发起了纪念宣传活动来启蒙社会。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列宁将沙皇的名字换之以莫尔、坎帕内拉、傅立叶等人的名字。1918年,塔特林的支持者普宁(Nikolai Punin)表达了构成派的倾向。他说:“无产阶级将创造新住宅、新街道、日常生活的新事物。无产阶级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懒惰供奉的神殿,而是一种生产新艺术制品的工厂”[9]。1919年苏联政府艺术部征请塔特林设计了第三国际纪念塔。1921年斯台帕诺夫(V. Stepanova)第一次在演讲中使用了构成主义这个词。在罗辰柯(Rodchenko)组织的构成主义第一工作组中,构成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式形成。他们试图在社会主义框架内通过将艺术和技术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方法,创造一种理想的、新颖的、平均主义的世界。他们抛弃有关品位、鉴赏力和构图的概念,认为那是过时的资产阶级的评论标准,从而将自己置于一种不是有关风格潮流而是关注方法的设计。他们认为新技术需要一种组织的艺术和真正的构成。构成主义者们呼唤“生产制造的艺术”,他们认为新环境不仅要用最新的材料和技术,而且要用“功能”方法来设计。这种“功能”方法需要对使用者的需求和每一个活动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建立不同的功能和优化布局。有了对使用者的这种了解,就可以使用标准件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来经济和有效地满足各种构造/成的需要。
1920年代苏联经历着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和建筑高潮,使得构成主义有关工业化、标准化的建筑思想有了实现的市场,就连柯布西耶在访问了苏联以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克鲁替考夫(Georgy Krutikov)在“通讯空间走道上的城市”的方案中设想将工业基地设在地球上,而人们居住于外层空间的结构上,人们可以搭载独立的插座式飞行和生活单元来去于地球和空间结构之间。
法国在20世纪前期有关理想城市和乌托邦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加尼尔(Tony Garnier),尤其是柯布西耶的设计和著作上。柯布西耶的城市乌托邦主要表现在他1922年设想的“为三百万人居住的当代城市”作品中。该作品在1922年巴黎沙龙秋季上展出,它是一个一百平方米的模型。该城市设想的平面是对称的,它由两条垂直的高速公路在城市的街道网络中心的多层终端相交。下面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铁站。其上是一个铁路终端站,而屋顶则是飞机场。他的设计是基于这样的信仰,那就是现代城市,社会的中心不再是宫殿或是宗教场所,而是交通、通信和交换场所。这种中心在柯布西耶的城市设想中被24座60层高的高层建筑所围绕,它提供了一个由50~80万工作人口组成的行政和商业中心。这24座高层建筑是城市和区县的大脑和枢纽。但是,柯布西耶的计划和设想并没有从他所希望依靠的商业巨头那里得到支持,使他原来寄希望于从资本主义商业集团那里获得作为社会改良力量的希望彻底破灭。从此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城市结构进行改变,他认为首先需要有一种新的政治结构,这样才能保证城市结构的改变得以进行。他的新的标准世界需要一个中心化的工业结构,一种强力政府和政治。在这种世界中,个人的提案必须服从整体的计划,行政当局是最重要的。一种军事风格的组织,就如同军队中将军作为整个组织的行政领导,一个强有力的,绝对的政治领导,一个公共工程的行政领导,他可以强制性地执行将社会和城市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新秩序。这样他就将自己卷入法国工团主义运动,成为权力和独裁主义(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信仰者。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他所展望的新世界。1928年他甚至为法国右派集团写小册子,在‘La Ville Radieuse’中,他使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集会照片,并付之以如下的标题“一点点地世界逐渐接近它的终极归宿。在莫斯科、柏林、罗马和美国,民众们聚集在一种强烈的思想下”。柯布西耶在1928~1929年将他的思想送交苏联政府,1934年送交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941年送交法国维希傀儡政府,但是并没有一位独裁者愿意将他的思想付诸于实践。
同一时期内,赖特在美国试图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存秩序进行挑战。实际上赖特、柯布西耶和霍华德等人的理想城市的设想都有一套变化巨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纲领。1935年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工业艺术展中,赖特展示了他的理想城市模型,那就是“广亩城”。这是一个极端取消主义的城市模型,如果将广亩城与霍华德的“花园城”相比较,花园城市便显得十分传统。研究广亩城的人们会发现其实广亩城并没有什么城市,相反它具有的是一种反城市思想。在广亩城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已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工业城市是对人类的一种剥削,他强调自然的建筑和城市,一种有机的概念。他认为对土地的拥有制度是造成极大的不平等的原因。他响应杰弗逊所认为的真正民主的获得只有在所有的人都是土地的拥有者时才可能获得。在赖特的理想乌托邦城市中,每一个市民都至少拥有一公顷土地用于耕种和建造房屋,一半时间在工厂或其他专业工作,同时还有时间进行自由思考和脑力活动。他设想的广亩城试图将城市引进乡村。当然如同其他乌托邦设想和作品一样,赖特的广亩城设想在美国并没有反响,美国人对他的设想保持着一种盲聋状态。因为乌托邦梦想更好的世界,但并不接受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秩序[10]。广亩城还反映了赖特对个人自由的绝对信仰,他坚持个人主义的原则和倾向从而与传统乌托邦的走向大相径庭。他的实践 促进了当代城市建筑乌托邦所进行的极端自由(主)化和多样化的探索。
4.当代城市建筑与乌托邦
20世纪中期,尤其是60年代前后曾经是建筑设想和乌托邦方案层出不穷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对巨型结构的设计上,例如崇尚高技术和空间仓体形象的伦敦阿基格拉姆派。这时期的建筑师和设计者并没有思考具有普遍性的、理想工业社会和机械时代的建筑和城市形象。他们仍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他们接受了现代主义对工业消费社会的信仰,相信物质进步,相信逐渐提高的机械化程度能够解放劳动力,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休闲时间。英国和日本在该时期出现的有关仓体和插座建筑和城市便是根据工业化的预制和大规模生产,结合有关新科学技术的幻想而产生的。由柯克、超克、格林、哈伦、维布和克兰顿(Dennis Crompton)组成的阿基格拉姆集团使用波普艺术结合科学技术幻想和城市建筑设计,他们提出了骨架式的巨型结构作为提供水电等基本设备服务,而住宅、商店、办公等单元可以插入该巨型结构。这时期的作品以柯克等人的“插座城市”和哈伦的“行走城市”为代表。与此同时,以纽文华(Constant Nieuwenhuys) 为代表的情景主义(Situationism)试图带来城市和社会根本性的变化,创造一种适合后工业社会的环境。他们将现存和先行存在的要素按照新的文脉和关联域重新组织起来,他们认为逐渐增加了的机械化需要一种新的空间环境,这是一种系列情景,一种对“暂时性”存在和生活气氛的营建。情景主义与社会改造也有着联系,1968年法国社会动乱就与情景主义运动有着文化和思想上的关系。当代城市和建筑乌托邦继承了霍华德“花园城市”所开创的反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倾向,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创造的能动和自主性。这种注重个人权益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尤其反映在情景主义、超社、都市建筑社、索托萨斯、库哈斯和伍兹等个人和团体的城市和建筑乌托邦的畅想中。
索托萨斯(E. Sottsas)在1970年代的一系列乌托邦作品则具有诙谐、戏弄、调侃和嘲讽的特征。例如在1973年他绘制了一系列具有波普艺术性质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对那些著名的和有影响力的当代建筑思想和概念进行嘲弄。他最喜欢将那些崇拜和信仰无止境线性发展的技术进步的乌托邦作品作为靶子进行戏弄。在他的作品中,时间和自然最终征服了所有这些乌托邦幻想;在他的作品中阿基格拉姆派的“行走城市”似乎被遗弃在一个荒芜、废弃和终止了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运转,更不用说机器了。轨道城市是1960年代乌托邦建筑的热门概念。而索托萨斯的“轨道城市”则犹如一个没有生命的长虫倦伏在丘壑上[11]。此外,超社(Superstudio) 、都市建筑社(OMA)和库哈斯(Rem Koolhaas)在1970年代早期都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乌托邦城市设想或批判性的城市方案研究,尤其是库哈斯的研究和方案较为完整。但伊顿的著作对当代乌托邦的研究稍有不足,除了没有论及索托萨斯,对1970年代以来的城市建筑乌托邦的活动,尤其是对库哈斯的作品缺少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研究,也没有对伍兹的乌托邦城市和建筑思想进行介绍讨论。下面对这两位建筑师的作品进行一些补充。
库哈斯的早期作品是与他在都市建筑社的主要成员独立但是又是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研究的主题仍然是曼哈顿。都市建筑社的一些作品的走向与索托萨斯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怀疑态度相似。例如Madelon Vriesendorp的“自由之梦”表现了都市死亡的痛苦。这件以曼哈顿为主题的作品表现了核冬天的到来,世界似乎遭受了核爆炸,没有人烟,世界的一半是新的冰川世纪,另一半是电击雷鸣的荒漠。冰雪覆盖的曼哈顿惟一可见的是断裂的克莱斯勒大厦的塔尖,自由女神正试图从象征毁灭了的人类文明的克莱斯勒大厦中挣脱出来[12]。
库哈斯在1970年代对曼哈顿进行了系列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城市乌托邦作品。库哈斯的这些研究随后被系统的整理总结,并总结在《发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13] 一书中。在该著作的前言中,库哈斯认为曼哈顿令人着迷,它充斥了变异的建筑、乌托邦的片断和非理性的现象。曼哈顿的每个街区都笼罩着很多层的幻影建筑、放弃或半途而废的建筑方案和计划,以及大众幻想。这些内容构成了另一种与现存纽约城不同的形象。因此他认为曼哈顿是一种没有宣言的乌托邦,它充满着乌托邦的证明,但是并没有公开发表的宣言。库哈斯的《发狂的纽约》试图根据曼哈顿的城市建筑历史和现状发表一个回顾式的宣言。这是一种对曼哈顿的解释,一种对曼哈顿城市工程和纲领的回顾式的寻求和塑造。他特别强调在1890到1940年之间,一种新的文化(机器时代的文化)选择了曼哈顿为其实验场。人们在曼哈顿进行了都市生活风格的创新和实验。由此,曼哈顿的建筑就可以作为一种集体实验。在这种实验中,整个城市就成为一个真实和自然停止存在的人造实验工厂。
“缩影世界的城市”是库哈斯的乌托邦代表作。在该作品中库哈斯致力于探索对人工概念、理论、解释、心智构造、假设和建议的产生对世界的影响。他设想的这个城市是“自我”的首都。在该城市中,科学、艺术、诗和疯狂的形式在理想的条件下竞争,去创造、毁灭和恢复令人吃惊的非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种科学设想或无端的臆想都有一个基地、一块实验田。每个基地上都有着相同的由花岗石制作的基座。为了辅助和激发那种投机性的,敢于冒险的活动。为了创造一种非存在的物理条件,这些作为意识形态实验室的花岗石基础可以悬置不受欢迎的律法和不容置疑的真理。从这个坚固的基础出发,每种哲学都有权力向上无限地发展。从一些基础生长出完全确定的肢体,而从另外一些基础则生发出临时性的软结构。库哈斯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天际线的变化是快速和持续的,这是一种丰富的、令人吃惊的道德的愉悦、良心的发烧,或是理智的自慰。库哈斯认为他设想的这些“塔楼”的崩溃有两种意味:一是失败、放弃,或是一种视觉上的狂暴喷射。
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幻想和乌托邦集中表现在纽约建筑师伍茨(L. Woods)的作品中。他的乌托邦作品以作品集、丛刊专集和著作的形式发表。其代表性的著作是‘ONE FIVE FOUR’[14],1992年出版的《新城》[15],1993年出版的《战争》[16],《利布斯·伍茨》[17]。其主要建筑和城市乌托邦作品包括中心城市、地下柏林、空中巴黎、独屋和柏林自由区。
他在“中心城市”这件作品中设想出人类和社团的不同活动,并为这些活动准备的相关建筑组成了一个个的中心。每个中心城市在平面形式上呈现为不完整的圆周状。多个中心城市组织在一起形成城市网络。中心城市中的建筑是一种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工具,是为一种探索和实验性的生活服务的。这种工具式的建筑可以辅助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辅助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对视觉、触觉等感觉系统的探索和尝试。由此,建筑就成为“实验室”,生活在中心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就具有探索性和刺激性。于是,一种新生活方式,实验性的生活就与一种新城市建筑,中心城市结合起来了。什么是“实验性的生活呢”?伍茨的解释是:“实验性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吸收知识的条件上生活”[18]。因此,每个人和社团就要不断地自发和巧妙地掌握和发展自己的知识,同时要不断地走出知识的极限去获取和探索未知,从而不断地在生活中进行实验。他认为在目前的技术社会中,创新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传统。新的生活知识和条件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人们无法有效充分地了解、测试和估量它们,也无法有效充分地掌握它们。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思维的突变,变化就很可能导致新的城市,例如“中心城市”式的城市的出现。无论如何,建筑师将在人类未来社会的创造中起着比今天更大的作用。他说:“我相信如果建筑师面对新知识、新技术、新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就会试图改变目前这种附庸地位,去创造一种新世界”。[19]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伍茨的建筑创作是以自我命题的方式进行的,但后来他经常应邀进行创作。在这些受邀之作中“地下柏林”(1993)方案令人注目。在这件作品的设计中,他认为每个城市建筑方案均伴随着特定的社会需要、社会功能和社会组织。“地下柏林”为柏林人提供了一种新生活方式。他认为人们的生活目的、手段和方式与世界的物质和物理条件相联系,地下生活也是如此。地下有一系列的物理力的特殊条件,如地震力、引力,以及在地球内部互相作用的电磁力。他设想的生活方式试图对地下的物理条件做出回答,他设计的地下城市建筑由薄膜金属制成,并用很精致微妙的机械和材料加以分割。这些地下结构很像精密的机械仪器。这些仪器与地质力学以及地磁力的频率相协调。他说人们或许听不到甚至感受不到这些,但在思想层面和电磁现实中,人与地(宇宙)的和谐通过机械获得了。该方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地下世界。该地下世界由一个巨型球体空间组成,该空间为他上面所说的精致的建筑机械提供了地下实验场所,为人们的“实验性生活”提供了场所。地下球体空间为辅助人类实验性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特定的辅助手段,这些辅助手段就是伍茨设计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金属平台,这些平台构成地下空间之间的市政联系。于是,“地下柏林”就成为一系列生活实验室,建筑要素成为居住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的机械。
“地下柏林”方案结束后,邀请者又请伍茨为21世纪的巴黎提出设想方案,题目拟为“巴黎:建筑 + 乌托邦”(1994)。伍茨在谈起“空中巴黎”时说:“设计时自然地想起上次在‘地下柏林’。我对‘柏林方案’的最后记忆是那些冲出地表飞向空中的建筑要素。它们飞向何方呢?就让它们飞向巴黎吧。我设计的这些飞行器将在巴黎上空聚集。对我来说柏林是个内部的室内空间,是地下的、内向、封闭和地表的世界。巴黎则是一个充满阳光、空气的城市,一个飘渺的轻质世界。”他设想在巴黎上空组装那些由薄壳材料制成的机械片断和构件。随后开始设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构造手段,以及如何将这些漂浮在空中的轻质结构与地表联系起来,如何将它们固定起来。他认为“空中巴黎”的关键是如何使这些部件悬浮在空中。首先,这些结构和部件与飞机不同,它们没有引擎,只是一种漂浮物。他使用“磁悬浮”的概念,设想这些空中悬浮结构是一个双磁体,它借用地球磁场来漂浮停留在空中。这样,‘空中巴黎’是一件随风摇曳的空中结构,这些部件由结合成网状系统互相支撑的缆索结构系在埃菲尔铁塔上。
他设想这种结构是为某种如同马戏团那样的社团服务的,居住者如同杂耍,这群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流。伍茨认为这种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它是没有传统秩序、结构、中心和等级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人们要有充分的“实验性生活”的精神,因为新生活充满刺激冒险和探索,要不断地面对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是一种在新技术条件下冒险的乌托邦世界。伍茨的方案通常考虑的是大尺度的城市社会,但他也试图返回到较小的独立结构系统中去尝试和检验那些宏大的想法是否合理可行。独屋就是这种尝试的产物。该结构内外没有梁柱支撑,结构是由建筑形式衍化而来到,其内部也没有进行功能分划。在伍茨的世界中人们得以发现一种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世界”,该世界有时表现出一种完美的特征,有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新奇的特征,有时甚至使人震惊和恐惧。
奥地利实用美术馆主任诺埃瓦(Peter Noever)说伍茨的作品“对现存建筑状态持批评态度。伍茨的批评态度是一种打破一切的态度……。他的作品形象具有一种真实、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又使人感到一种解脱,一种精神上的解放。”[20] 这位站在建筑学边缘的形而上学的建筑师走到想像的极至。他创造的建筑世界虽然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的世界却使人耳目一新。伍茨之所以提出这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主要是他对现存建筑状态的不满,他认为建筑的现实令人感到悲哀和可怜。他对建筑现状的分析和批评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的,他称“建筑是一种政治活动”。他认为目前西方建筑师实际上是现存社会政治结构的建造者,因为建筑师遵循那些已存在的,表现某种阶层压制另一阶层的隐藏形式,或遵循那些隐藏在得益于现行常规、秩序和习俗的社会形式,而居住者则永远是最后被建筑师考虑的。居住和使用者不得不接受建筑师和顾主以及现行社会习俗强加的东西。这样,居住者承担着所有的上层建筑的重负。
伍茨要创造一种新城市和建筑,他自认这些年来的作品是在创造一种新观念的建筑。这种新观念就是他所称的Terra Nova. 他说:“Terra Nova有两个意义,第一它具有某种新鲜性,主要指‘新’的地球具有某种奇异陌生性。当我们面对新奇、陌生和不熟悉的事物时,我们受到震撼,感到吃惊和不安。陌生和奇异性使我们从熟悉的思考方式中走出来,去面对现实。这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来说十分重要;第二与人类的天性有关……人类的天性就是去创造和构造自然。我们必须创造世界以便彻底地在其中生活。”他称“在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承诺,那就是不仅对那些为现存生活方式服务的建筑感兴趣,我更感性趣于一种尝试,一种新的可能的生活方式。”[21] 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建筑权威。他说他只感兴趣于个人行为的权威,注重个性和个人探索,尊重每个人的行为自由、探索自由。他又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权威能够延续很久,因为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短暂的。在这种朝夕变化的美学世界中没有一种形式或个人能够将权威保持长久,这种美就是他称道的“存在美”。他认为在这种世界中建筑的任务和作用就应该如同工具的作用,是工具性、手段性的,而非表现化的,建筑应该是延展个人活动、思维、理解能力和极限的工具。
当代建筑和城市乌托邦设想如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乌托邦实践一样都是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组成部分,是历史上各种追求理想社会的设想和实践的延续。它更继承了早期现代主义那种对理想社会和城市建筑的追求,保持了早期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憧憬和所充满的那种信心。同时它也对现代主义理想中所具有的缺陷,以及今日社会生活和城市建筑中所具有的问题提出批评,并提出自己的乌托邦方案用以解决上述缺陷和问题。已故美国城市和建筑历史学家芒福德曾说“一幅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看”。他的话当然不是有关地图的,而是有关城市与建筑的。
注释:
[1] 见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2] Joyce Oramel Hertzler,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3] 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4]Robert Fishman,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benezer Howard, Frank Lloyd Wright, Le Corbusier (Cambridge and London, 1984), P.34.
[5] Le Corbusier, La ville radieuse. 转见于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156.
[6] [7] A. Sant'Elia, 'Manifesto of Futurist Architecture'. In U. Apollonio ed., Futurist Manifestos (London, 1973). 转见于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182.
[8] A.A. and V.A. Vesnin, 'Tvorcheskie otchety', 转见于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183.
[9] N. Punin, 'Meeting ov iskusstve', 转见于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187.
[10] 参见Robert Fishman,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benezer Howard Frank Lloyd Wright Le Corbusie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2).
[11] Ettore Sottsas, 'Walking City, Standing Still'. AD 3/4-1985.
[12] OMA/Rem Koolhaas & Madelon Vriesendorp, 'Dream of Liberty'. AD 3/4-1985
[13] Rem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4).
[14] L. Woods, OneFiveFou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9).
[15] L. Woods, New C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or, 1992).
[16] L. Woods, Wa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3).
[17] Architectural Monographs No. 12: Lebbeus Woods (Academy Edition/St. Martins Press 1992), pp.8-18.
[18~22] Peter Nouver, 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 (Prester Pres, 1991).
本文原载《建筑师》116期,授权ABBS刊载,禁止转载。 |
|
[更多评论]
[更多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