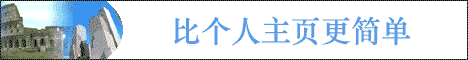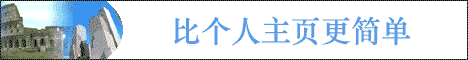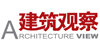
□ 刊发于
《建筑观察》
2009年第06期
|
|
|
罗德胤、胡新宇访谈录
本刊
|
罗德胤、胡新宇访谈录
罗德胤 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胡新宇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顾问
古建保护在学科上 有难以解决的漏洞
建筑观察:现在国内的文物保护都打着“可持续发展”的旗帜,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罗德胤:咱们国内对文物保护的态度大体是立足于所谓“可持续发展”,但这个“可持续”都是着力于自我的可持续。具体来说,就是保护要建立在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的基础上,挣钱的主要手段就是旅游。因为害怕投资难以收回,所以基本的态度是赶紧挣了再说,尽量多挣、快挣。这对文物建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建筑观察:但是现在很大的问就是很多地方把这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可以作为旅游资源的东西给拆了,比如喀什,将古城拆了,建新城,然而就喀什的区域位置和自然资源,除了旅游又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胡新宇:这就是短视么,当然,他有很充足的理由,地震,老房子抗震性能差,他们需要建一批安全系数高的新房子。
建筑观察:其实这些官员们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想法和认知程度不比咱们差,可他们还是这么做。
胡新宇:我很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在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顽固。罗教授你同意么?
罗德胤:可能他们自己都不能左右,因为我们现在上了一辆“发展”的列车,谁也不能违背“发展的规律”,一切都要尽量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既然我们确实需要发展,又真的需要改善生活,所以对老房子动点手术就是“不可避免”的,是理所当然的。
建筑观察:关键是现在动的不是小手术,都是截肢。
罗德胤:对,因为古建保护在很多时候就是手术动得越大越容易,最好是抹掉重修,最简单,时间也最短。这也和官员任期有关系,一定要在任期内尽快解决,否则一来对官员本身的政绩有影响,二来不可控,谁也不知道下一届官员对此什么态度。这就导致要尽快解决,所以就需要动大手术。在历史建筑保护得好的国家,古建保护的技术和程序比较完善,通常把保护修缮的计划定得比较长,比如先定小规模的三年计划,然后再是十年计划,再是二十年计划。建筑保护和文物保护有很大的差别,文物保护非常严格,赝品就是赝品,唐伯虎临摹的宋画就是唐伯虎的画,不是宋画。建筑和文物就不一样,比如一个房子的一角被雷击损害,你修还是不修呢?修的话即使你修旧如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角就是赝品。所以,古建保护在学科上有难以解决解决的漏洞。
建筑观察:不过对于古建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继续有生命力的生长。
罗德胤:这话听着好,但其实容易被人利用,甚至是有意地误用。既然一个角可以重修,为什么整座建筑不能重修呢?慢慢修的话可能需要十年,拆掉重修的话十天就够了,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我们中国又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整个重修的做法尤其受到执政者的青睐。就像前门大街,拆掉重建可能是最快可以见到经济效益的办法了。在“领导”眼里,只能这么做,这是“唯一”的办法。
建筑观察:故宫属于独立隔离的保护,但是像一些老城区,比如东四等老居民区,还有人们住在里面,而他们的设施又很落后,这也是一个矛盾啊。
罗德胤:对,设施可以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可能有限。比如,电灯可以进去,给排水管线可以进去,卫浴完全可以做到和现代建筑一样,但是很多老建筑的采光、隔音都有问题,并且空间狭窄,和一些现代的家具有冲突。这些老房子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过如果想再提高生活水平的话,那就必然对旧房子的历史真实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必须搬到新房子或者必须拆掉重建。
建筑观察:您觉得目前我国历史文物建筑保护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漏洞?还是公民意识?还是体制?
罗德胤:我觉得宏观地说是体制问题。比如澳门,他们做得很好,负责文物保护的技术官员二十年没有换人,职务不变,工资年年涨,所以他们的文物建筑保护就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而不会出现换一个行政长官就换一种保护思路和保护态度。公民意识是要培养的,但从某种意义上,城市的管理者其实是不希望大家具备这种意识的。因为有些东西是必须为所谓的经济发展(其实很可能是强势阶层的经济利益)让步的,而这种意识可能会造成一些工作上的难度。文物建筑保护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了,虽然它有漏洞——既然这个漏洞是没有办法完全弥补的,那就让我们尽量弥补吧,做不到100%,99%也行,逐级退让,直到不能再退为止。文物建筑保护和国民教育有很大关系,但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也和中国的软实力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的钱都用在发展上,创造GDP,很少把钱投在文化建筑保护上,即使有投资,也是希望能有回报,或者初期给你投入了,之后你就可以独立运营了。当然,这比没有好,不过基本态度没什么改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为基本的义务。一个家庭不遗余力地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父母想过要什么回报么?可现在管理者没却没有这样的意识。澳门为什么做得好,因为他们每年的预算都是定额的,这些钱就是要花在公共文化的维护上的,他们讲求的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说白了也很简单,专门有这么一个人,负责这些款项用途、文物修缮,并且建立了很有效地审核监管机制。
胡新宇:国外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做Political management of public——公共政治管理,而国外的NGO、博物馆都属于公共政治管理的范畴,专门培养一部分人从社会的全局来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乡土建筑的保护机制
建筑观察:罗教授,您所在的清华乡土建筑研究所都做了哪些工作?
罗德胤:我主要做的研究和评判工作,比如一座文化遗产建筑,要100%保护是不可能的,那就得退让,哪些可以退让,什么是底线,这些就要对他们有个历史价值的判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这些建筑的历史价值,主要是古建保护的前期工作,偶尔也会做些保护规划。
建筑观察:那乡土建筑的保护和北京这种古城内古建的保护面临的问题有什么区别么?
罗德胤:从大的方面来讲,没什么区别,不过相对来说乡土建筑面临的经济压力小些,城市里面地价太高,附加价值和开发价值高,所以保护的经济压力大些,而乡土建筑面临的是当地居民的自己的毁坏和建筑物得不到妥善维护的困难。
建筑观察: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偏远地带,乡土建筑的保护对当地居民很难产生有效的经济意义,因为乡土特色旅游做得好的只有那么几个地方,不可能全部用来开发旅游,那么我们怎么能解决这部分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乡土建筑保护问题呢?
罗德胤:从国际经验来说基本上是靠两股力量,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社会力量,就像胡老师这边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企业也会捐一部分资金。
建筑观察:但是企业更加注重广告效益,他们捐资给北京这样的古城,收益更大一些,而这种偏远的乡土建筑,是不是对他们构不成吸引力呢?
罗德胤:也不一定。就像浙江诸葛村,有很多在外经商的,他们会集资对家乡建筑做出一些保护性工作。岭南地区的侨乡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求一种文化认同感,寻根的情结,所以他们对家乡的乡土建筑看得很重。而从政府层面来讲呢,他们希望这些文物建筑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特别是对文物建筑这种没有直接产出的东西,所以就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将这些经济压力转嫁到民间资本身上。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生长这种民间力量和组织的土壤,所以,文物建筑单位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自给自足是最理想的,而旅游是最合理最可行的方式,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周庄,如果学不好,那是你自己的原因,怪不得别人。
7号院和芭芭拉四合院是两个特例
胡新宇:几年前,我去黔西县,有个千山观,改造还算是成功,属于政府出面,商业操作,从古建保护角度来讲也可以接受。原来2万m2的一个古堡,城堡的一部分就是长城,前几年政府来出资进行维护修缮,每公里10万元,当地的旅游局和文物局合并了,那个局长的意识还是很好的,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比较保守的就是原样保护,内部修缮;另一个做成了娱乐城,把宿营、娱乐都引进来,成了杂货铺。我们过去给他做咨询,建议他还是做中高端,原样保留恢复,他们还是对我们的意见很尊重的。第二年再去看就已经改造完了,风貌也都恢复了,并且内部设施也都作了很好的改善,基本上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但是保留了很原始的风貌。应该算是古建再利用。
罗德胤:这种做法在文物建筑保护得好的国家也许是完全禁止的,可在中国目前却可能被视为是最理想的。从道理上说,只要一列入文物建筑,就不能随便乱动。修缮要非常慎重,建筑构件不能随便落架,能加固就加固,如果实在需要替代,那也需要对材料进行精细的研究分析,找尽量接近的和原来的匹配。我们对这种改造模式也是怀着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它确实是保护了老建筑的风貌,也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它确实又把老东西给毁了。而在中国,声音最强的就是这种模式,他们自认为掌握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真理,满足了方方面面的需要,无懈可击,但是这实际上对古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破坏。
胡新宇:那你所理想的模式呢?
罗德胤:我们所理想的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太难实现了。(这个话题我没来得及展开。其实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实例,那就是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胡新宇:那这个和中国建筑的本身特点有关系么?
罗德胤:没什么关系,木构件也能得到很好地保护,主要是体制和观念的落后,因为我们意识不到它的价值,大家没有用文物的标准来要求文物建筑,而文物建筑本身又有这方面的漏洞。
建筑观察:国外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并不是指的经济价值?
罗德胤: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他们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家当,是祖先传下来的,所以叫做“文化遗产”么,作为一个民族,祖先传下来的,我们有责任传给下一代。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美保护措施就是这样的,尽量不去破坏它和改变它,我们这一代没有把握做得完善,那就留给子孙有能力的时候去做。
建筑观察: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们国家的文物管理者们想把这些传给下一代,但是我们的经济和能力制约,导致这件事情不成功?
罗德胤:这些都是借口,现实确实有困难,但不足以让人妥协。中国建筑师又特别“善于”寻找妥协的方法,在旧建筑的改造利用上也确实下了很多功夫。不过这种声音太强大了以后,就相当于鼓励造假了。原来我们批判造假,是因为造得太差,而现在有一批造假技术很高的人,造得很逼真很漂亮还有品位,于是大家就认可了,就成为现在中国通行的做法,最被接受的做法。但我相信这种做法几十年之后将会被重新评判,几十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就会追问到底原来什么样,而不是现在的漂亮东西,漂亮东西可以再创造,但真正的老东西、老建筑,再丑,再破也是代表了一种历史真实性。
建筑观察:就怕以后的孩子被现在的假古董所迷惑了。
罗德胤:有的恐怕不会被迷惑,因为有文献记载,有据可查。没有文献记载,无据可查的,人们也会怀疑其可信度。
胡新宇:不过公众在某一时期会被左右和迷惑的,因为目前大家觉得这种模式好,缺失了对历史文物的评判标准。除了“造假”,将古建私有化保护也是一种方法。我观察到两个不错的案例,一个是7号院,一个是德国人芭芭拉在后海买了一个140m2的四合院,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维修,7号院面积为1800m2,用了3年的时间,这个工期在北京是不可以被接受的,这两个案例属于特例。
罗德胤:如果他们对古建真正理解了的话,也许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这两个项目这么慢?是因为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把四合院作为自己的资产,所以非常认真,每一步都很慎重,没有把握就会停下来细细研究,大量时间花在思考和做研究上了。其实如果是很有经验的修复工匠,不会花这么长时间的。
罗德胤:河北蔚县灵严寺请我们做保护建议,我给他们的建议是暂时别修,只要打扫好卫生,就可以大搞旅游,可是这些在对我们看来最理性、最节约的保护办法,对他们来说却可能是不可行的,因为种种原因,地方上一般都着急着上项目。
胡新宇: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旅游的概念,不知道怎么推广。
建筑观察:现在还有些建国以后建设的建筑,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也应该有保护价值吧?100年后也会成为文物建筑。
罗德胤:价值是肯定有的,不过什么该保护,他们的历史价值在哪,都得到那个时候说了才算,现在去评价还太早。我个人对这个问题还来不及思考。
建筑观察:798现在是一种保护再利用的模式,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复制这种模式。
罗德胤:这是一个特别的方式,并不是人们事先能设想的,798也是自己生长起来然后受到大家注意的。现在很多地方在仿照它,有的也能成功,有的就不能,那还得去考虑别的出路。古建筑再利用是一个方向,这没错,但是要为了再利用却对其历史真实性造成损伤的话,就有违再利用的初衷了,首先要保下来,然后才是经济利益,如果要舍弃初衷而追逐经济利益,就舍本逐末了。
没有孩子之前看不到孩子
建筑观察:那胡老师那边的民间组织,您有什么看法?
罗德胤:他们很伟大,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在做的事情对中国当前以及以后的文物建筑乃至文化保护,都有很大的意义。虽然他们做的工作相对于中国这个浩大的文物建筑大国来说微不足道,但是他们是一个标志,也是希望。
胡新宇:我的感觉是没做文化遗产保护之前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了这个行业,就会刻意地去找,发现身边还是很多的。其实很多古建保护的问题还是和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的,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民素质提高了,自然就会关注这些事情。
罗德胤:没有孩子之前看不到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满大街都是孩子。 |
|
|
|